構(gòu)建“2+1 ”部門內(nèi)生創(chuàng)新模型,考量政策的連續(xù)性和制度的穩(wěn)定性對經(jīng)濟增長產(chǎn)生影響。結(jié)果表明:由于創(chuàng)新活動具有極大的風險性質(zhì),初期需要巨大投入,而回報分散在漫長的未來時間,因而未來面臨的各種制度和政策變化都會影響到創(chuàng)新成果的現(xiàn)值,從而不利于鼓勵研發(fā)部門將資源投入創(chuàng)新活動。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部門需要實現(xiàn)多重政策目標,這意味著鼓勵創(chuàng)新的目標可能受到牽制,從而增加了創(chuàng)新活動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因此,要促進創(chuàng)新活動,必須為研發(fā)部門提供一個可以穩(wěn)定預期的未來制度與政策環(huán)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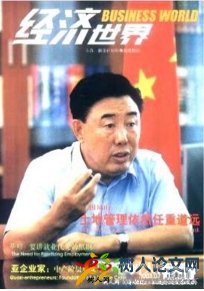
《經(jīng)濟世界》(月刊)1984年創(chuàng)刊,是由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辦的專業(yè)性學術(shù)經(jīng)濟報道刊物。介紹國外經(jīng)濟發(fā)展的經(jīng)驗和動向,以及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以經(jīng)濟新聞雜志的形式,向讀者提供有關(guān)國家經(jīng)濟的有深度的和綜合性的報道。
一、引言
當前中國經(jīng)濟正處于轉(zhuǎn)型升級的階段,供給側(cè)改革成為經(jīng)濟增長質(zhì)量提升的關(guān)鍵,也是引領(lǐng)下一波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的必要途徑。 相應地,創(chuàng)新驅(qū)動就成為未來經(jīng)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理論上,內(nèi)生經(jīng)濟增長理論將技術(shù)進步內(nèi)生化,成功地分析了技術(shù)進步與經(jīng)濟增長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各國在經(jīng)濟增長過程中人均收入得以趨同的條件是什么,從而分析哪些國家在趨同、可能趨同,哪些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沒有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技術(shù)進步,經(jīng)濟增長會大受制約,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會不斷擴大。
中國的創(chuàng)新活動與美國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美國創(chuàng)新活動最為活躍的公司如微軟、谷歌、蘋果、IBM、英特爾等在數(shù)量上遠遠多于中國,在技術(shù)水平和技術(shù)專利上也遠遠領(lǐng)先中國。而中國大量的資本資源投入到房地產(chǎn)、金融等能夠快進快出的領(lǐng)域,致力于“百年老店”事業(yè)的投資少而又少,認真進行創(chuàng)新活動的企業(yè)也屈指可數(shù)。
現(xiàn)有文獻在分析創(chuàng)新活動的形成機制和對經(jīng)濟增長的影響上基本達成共識:創(chuàng)新是持續(xù)經(jīng)濟增長的動力。關(guān)于創(chuàng)新形成過程,主流文獻從三個角度展開了分析:(1)將創(chuàng)新內(nèi)生化,將其看成是企業(yè)追求盈利動機的結(jié)果。Romer(19 90 )將內(nèi)生的技術(shù)變化引入經(jīng)濟增長模型中,從企業(yè)的盈利動機來分析技術(shù)的進步問題。他將經(jīng)濟分為最終產(chǎn)品制造部門、體現(xiàn)新技術(shù)的中間產(chǎn)品制造部門和研發(fā)新技術(shù)的部門三個部門,討論了研發(fā)部門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活動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向最終產(chǎn)品部門轉(zhuǎn)讓技術(shù)而促進經(jīng)濟增長的[1 ]。Lucas(1 988 )分析了人力資本的生產(chǎn)過程和對經(jīng)濟增長的影響。他假設(shè)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驅(qū)動下將勞動力配置到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上,而人力資本的積累具有外部性[2 ]。Aghion 和 Howitt(1 9 92 )受熊彼特創(chuàng)新思想的啟發(fā)提出了創(chuàng)新性毀滅的經(jīng)濟增長模型,實際上這個模型是熊彼特理論的重新表述,是將其理論納入到內(nèi)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中。他們強調(diào)了創(chuàng)新的風險性質(zhì):投入巨大資源研發(fā)出來的新的技術(shù)隨時有可能被更好的技術(shù)替代,從而喪失其價值。 這種性質(zhì)就使得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經(jīng)濟增長無法實現(xiàn)帕累托效率[3 ]。(2)從制度和社會的角度分析了創(chuàng)新的形成機制。Baumol(19 90)、Murphy 等(1 9 9 1 )認為,創(chuàng)新是那些杰出人才完成的工作,而且創(chuàng)新對這些杰
出人才而言只是多種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活動中的一種,杰出人才需要決策的是,是否從眾多高難度活動中選擇創(chuàng)新。同時,針對那些杰出人士提供經(jīng)濟動力并在制度結(jié)構(gòu)上加以約束和引導,對鼓勵創(chuàng)新活
動而言是極為重要的。(3 )考慮了制度和政策不確定性對創(chuàng)新的影響。 Lueg 和 Borisov(2014 )強調(diào),企業(yè)所進行的創(chuàng)新活動必須對環(huán)境的變化做出相應反應[4]。Mcmullen 和 Shepherd(2006 )強調(diào)了企業(yè)對不確定性的態(tài)度比不確定性本身更為重要,如果企業(yè)能夠積極面對不確定性,將有益于企業(yè)對創(chuàng)新決策的制定,從而增加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行為[5 ]。 王俊雄和王建華(201 6 )指出,政府應想辦法為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行為提供保障,從而減少企業(yè)對于不確定性的顧慮,強化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主體地位,支持企業(yè)創(chuàng)新能力
提升,完善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制度環(huán)境,推動企業(yè)創(chuàng)新[6 ]。王亞妮和程新生(2014)認為,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動往往需要冗余資源的參與,而環(huán)境不確定性的增加有可能促進企業(yè)將冗余資源用于創(chuàng)新,環(huán)境不確定性在資源約束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并不能促進、甚至會阻礙企業(yè)創(chuàng)新項目的開展,而只有當企業(yè)資源
較為富足時,環(huán)境不確定性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積極作用才會得以體現(xiàn)[7 ]。郝威亞等(201 6 )研究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會致使企業(yè)推遲研發(fā)投入決策,從而抑制企業(yè)創(chuàng)新,因此,政府應當盡量穩(wěn)定市場對政策的預期,以緩解經(jīng)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負面影響[8]。黎文靖和鄭曼妮(201 6 )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選擇性產(chǎn)業(yè)政策并不能激發(fā)企業(yè)進行推動技術(shù)進步和獲取競爭優(yōu)勢的實質(zhì)性創(chuàng)新,企業(yè)為了得到政府的扶持而選擇僅僅增加創(chuàng)新“數(shù)量”的行為只是一種策略性的創(chuàng)新[9 ]。
綜上可見,國外的文獻大多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探討創(chuàng)新的形成過程,這一點并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動的驅(qū)動力更多的是資本的逐利。此外,國外主流文獻研究的對象是以發(fā)達國家為主,它們有著成熟穩(wěn)定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而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是一個持續(xù)的轉(zhuǎn)型過程,這也意味著制度的不斷變革和政策的持續(xù)調(diào)整。這種環(huán)境對企業(yè)家而言意味著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創(chuàng)新活動是需要初始大量投入、后期緩慢回報的過程,因此,不可預測的未來就會制約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活動。國內(nèi)文獻雖然也有研究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對創(chuàng)新活動的影響,但是大多聚焦于個別具體的政策,沒有從主導這些政策的制度環(huán)境進行分析,而這正是中國經(jīng)濟增長與創(chuàng)新活動中的關(guān)鍵萬因方素數(shù)。據(jù)因此,本文將利用動態(tài)不一致性的理論,分析中國制度環(huán)境中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連續(xù)性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的影響。
二、創(chuàng)新促進經(jīng)濟增長的機制
(一)對中國經(jīng)濟現(xiàn)狀的模型設(shè)定:制造業(yè)與研發(fā)兩部門經(jīng)濟
將經(jīng)濟部門分為制造業(yè)和研發(fā)兩個部門,其中制造業(yè)即傳統(tǒng)部門,可以只借助資本與勞動開展生產(chǎn),也可以采用新的技術(shù)以提高生產(chǎn)效率;新的技術(shù)則來自研發(fā)部門,需要動用資本資源投入到研發(fā)活動中。雖然很多企業(yè)都自行設(shè)有研發(fā)部門,但是也有不少企業(yè)會購買其他企業(yè)或科研機構(gòu)研發(fā)的專利。
在這樣一個兩部門經(jīng)濟中,制造業(yè)部門遵循傳統(tǒng)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技術(shù),研發(fā)部門則需要兩個決策:先決定投資開發(fā)技術(shù),其成本為 C;一旦技術(shù)開發(fā)成功,就生產(chǎn)體現(xiàn)這一技術(shù)的設(shè)備 A,并銷售給制造業(yè)部門。
(二)模型的均衡解:創(chuàng)新水平的決定機制
在均衡時,資本投向制造業(yè)和投向研發(fā)部門的收益率是相等的,否則,資本會從收益率低的部門流向收益率高的部門。 在不考慮資本折舊的前提下,資本投向制造業(yè)的收益率為資本投入的邊際產(chǎn)品。因為制造業(yè)是競爭性的,所以,各個要素獲得其邊際報酬。于是,根據(jù)式(1 )可知,資本投入到制造業(yè)能夠獲得的回報率為:
可見,當制造業(yè)和研發(fā)部門決策都是盈利最大化驅(qū)動時,同時,當制造業(yè)為競爭行業(yè)而研發(fā)部門為壟斷行業(yè)時,最終投向制造業(yè)的資本資源是常數(shù),見式(9),而投向研發(fā)部門的資本資源受到政府政策()τ和勞動力人口的影響,是稅收的減函數(shù),是勞動投入的增函數(shù)。這也表明,政府關(guān)于創(chuàng)新的政策在促進或抑制創(chuàng)新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
三、創(chuàng)新的決策過程與制度不確定性的影響
(一)技術(shù)專利開發(fā)決策
企業(yè)研發(fā)成果的價值是其在專利保護期內(nèi)所能獲取的凈利潤,但是因為不確定性,它的專利隨時會被各種因素終止,或者新的技術(shù)取代它,使其過時。這就是熊比特所說的創(chuàng)造性毀滅。或者政府政策改變,導致其市場地位受損。 例如專利保護的弱化或者政府撤銷針對研發(fā)部門的扶持政策等,都會導致創(chuàng)新知識的價值受損。設(shè)想這兩大原因?qū)е乱验_發(fā)的專利知識的價值量變動遵循泊松過程,即在開發(fā)出來的專利知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每一個時點上都以ε的概率喪失價值,而這個概率與專利知識價值存續(xù)了多長時間無關(guān),那么,在經(jīng)過 t 時間后,這個創(chuàng)新專利仍然有價值的可能性為 e -εt ,從而可以計算一項研發(fā)成果的價值 (現(xiàn)值 )為
(二)政府部門與企業(yè)部門單向信任時創(chuàng)新活動的決定
在開發(fā)技術(shù)專利時,研發(fā)團隊要預期未來的制度和政策是否穩(wěn)定,一方面,政策是否穩(wěn)定體現(xiàn)在τ的大小上面;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制度性的變化導致研發(fā)成果的獲利性被終止,這體現(xiàn)在ε 受到的影響上。顯然,對τ做出決策的是政府,同時政府的決策也影響著ε。
似乎只要政府減稅或者補貼以支持創(chuàng)新就可以促進經(jīng)濟增長了。 事實上,政府的多重目標使得問題復雜化。如政府關(guān)心經(jīng)濟增長率與公共服務,而公共服務來自稅收。如果政府因為任期的問題而關(guān)注短期目標,那么,可以假設(shè)它的福利函數(shù)為:
福利函數(shù)表明,政府有一個最優(yōu)的經(jīng)濟增長率目標 g ∗ ,或者這個目標是考慮到環(huán)境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同時也有一個最優(yōu)的稅收增長率目標 g T∗ ,因為政府要考慮通過稅收來滿足各項民生指標。如果沒有約束的話,這兩個目標都能實現(xiàn)。但是現(xiàn)實中是存在約束的:如果征稅過多,一定會影響經(jīng)濟增長率;如果通過減稅促進經(jīng)濟增長,則有可能導致稅收減少———拉弗曲線所說的降低稅率可以增加稅收只適用某一個稅率區(qū)間,超出這個區(qū)間就是另外的情形了。
四、政府部門和研發(fā)部門互信的取得機制:
不確定性的消除與創(chuàng)新的形成前面的分析是假設(shè)政府部門與研發(fā)部門之間的互動是一次性的,研發(fā)部門長期存在,而政府部門因為政策制定者的任期是有限制的。如果在制度上加以調(diào)整,讓政策保持連續(xù)性,不因為主要官員的離任而人去政息,那么,政府部門與研發(fā)部門之間的互動
五、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以上分析表明:創(chuàng)新過程是內(nèi)生的,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創(chuàng)新過程是利潤驅(qū)動的,而且是通過資本資源的配置來完成創(chuàng)新的。 在利潤的驅(qū)動下,資本資源會配置到利潤率高的部門。只要研發(fā)部門通過創(chuàng)新獲得的利潤率高于制造業(yè)部門,則資本資源會持續(xù)流向研發(fā)部門。研發(fā)部門完成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會在市場上交易,被制造業(yè)部門采用,從而帶來生產(chǎn)率的提高。在均衡時,研發(fā)部門完成的資本投入是既定的,但是由于知識的規(guī)模報酬不變特性,既定的資本投
入促成知識技術(shù)按照一個固定比例增長,從而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按照人均 GDP 測度的持續(xù)增長。同時,政府部門的制度和政策影響著知識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而且這個影響也是內(nèi)生的。通過動態(tài)博弈的分析框架討論政府是否堅持政策連續(xù)性和制度的穩(wěn)定性,可以發(fā)現(xiàn)動態(tài)不一致性出現(xiàn)的可能性和條件,以消除動態(tài)不一致性、確保制度穩(wěn)定和政策連續(xù)的機制,從而消除研發(fā)部門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鼓勵創(chuàng)新,實現(xiàn)政府、企業(yè)共贏。
本文模型分析力圖清晰地描述中國的創(chuàng)新過程和對經(jīng)濟增長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到:制度的穩(wěn)定性與政策的連續(xù)性是鼓勵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重要保障。如果政府朝令夕改,制度不斷變化,那么,企業(yè)對未來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就不愿意將資源投向一次性研發(fā)投入巨大而收益獲取緩慢的研發(fā)部門中。從實際來看,我國創(chuàng)新過程存在著短期行為,存在著掙快錢的趨勢,就是因為企業(yè)不知道巨大的研發(fā)投入能不能帶來足夠的收益。 因此,政府應盡力保證政策的連續(xù)性和制度的穩(wěn)定性,讓企業(yè)對未來有清晰的預期。具體而言,應從如下幾個方面加以改進:
1 .加強法制建設(shè),貫徹法治精神,增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權(quán)力。 在政府高級官員任期制下,制度的穩(wěn)定和政策的連續(xù)其實難有保證。 因此,必須探索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掌握重大政策改革或者政策調(diào)整的立法權(quán)的機制,這樣或許能夠給予致力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的企業(yè)更大的信心。 例如,涉及到市政規(guī)劃的決策,必須認真由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而對于既定規(guī)劃的重大更改,必須立法加以限制,設(shè)定紅線,嚴格控制允許對既定規(guī)劃加以更改的條件,以避免朝令夕改,讓創(chuàng)新者無所適從。
2.改萬革方官數(shù)員據(jù)晉升機制和調(diào)動程序,確保其按照嚴
格的組織程序進行。現(xiàn)有干部管理體制下,官員由上一級組織部門直接調(diào)動,尤其是省級和副省級官員,隸屬中央組織部管理,調(diào)動頻繁,存在著行政官員未任滿一屆即根據(jù)需要調(diào)動的情形。這種頻繁變更導致了重大政策的不連續(xù)。因此,為了保證政策連續(xù)性,必須確保行政官員完成任期,不隨意調(diào)動。
3.對行政官員等政績考核不能只考核經(jīng)濟發(fā)展指標,還要加入公信力的指標———政策承諾是否兌現(xiàn)。在當前只關(guān)注 GDP 的考核機制下,由于動態(tài)不一致性問題,按慣例連任兩屆的地方行政長官傾向于只考慮任期內(nèi)的 GDP 和財政收入,不會關(guān)注是否會對下一任帶來負面影響,從而導致人走政息。如果在考核地方官員時賦予企業(yè)家對其政策承諾進行評估,是可以避免這一結(jié)果的。在現(xiàn)有的架構(gòu)下,可以參照離任審計的做法,考慮引入人大常委會對離任官員進行評估的機制,其中包括企業(yè)家對其的打分。
4.設(shè)置縱向司法體系,加強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目前的司法體系與地方行政聯(lián)系緊密,從而受到地方利益保護的壓力。地方利益保護的動機會削弱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因此,可以加強司法體系的縱向管理機制,增強其相對于地方行政的獨立性。可以設(shè)置巡回法庭的機制,或者比照審計署或中國人民銀行的體制,對專司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司法機構(gòu)進行跨區(qū)建構(gòu)。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