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討竺法護譯場中佛經(jīng)的書寫文化,以期了解早期佛經(jīng)譯場與經(jīng)典傳播的現(xiàn)象。通過考察初期佛教文獻、有紀(jì)年的考古出土文物,分析初期佛教書寫文化。以現(xiàn)存紀(jì)年最早的漢文佛經(jīng)殘片,西晉元康六年(296)竺法護譯《諸佛要集經(jīng)》為例,由其卷尾題記中的兩位主要人物——竺法首與聶承遠(yuǎn),探討他們在譯場中的功能角色以及早期譯場中主要筆受與書法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研究表明,竺法護與弟子不但翻譯佛經(jīng),同時也由中原向河西地區(qū)傳播。
關(guān)鍵詞:竺法護;佛經(jīng)書寫文化;竺法首;聶承遠(yuǎn);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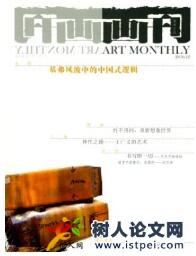
《畫刊》(月刊)創(chuàng)刊于1974年,是由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主辦的專業(yè)性的藝術(shù)雜志。30多年來已成長為著名的品牌雜志,在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享有盛譽。
一 前 言
敦煌寫本文獻的產(chǎn)生與佛經(jīng)譯場、寺院或公私寫經(jīng)坊的抄寫佛經(jīng)有密切關(guān)系[1]{1}。佛經(jīng)譯場組織,由兩漢至隋唐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的演變發(fā)展,直到隋唐時期才較為完備[2-3]。關(guān)于隋唐佛經(jīng)翻譯與譯場,前賢學(xué)者論著甚多,大多著重于佛經(jīng)翻譯者,此不贅述,但關(guān)于漢晉譯場中寫本佛經(jīng)的書寫文化,則較少涉及[4-6]。初期佛經(jīng)譯場組織還未定型,寫經(jīng)體與書寫文化也還未規(guī)范化。此階段譯場中的書寫文化可見于早期的經(jīng)錄與僧傳典籍,例如南朝僧佑《出三藏記集》與慧皎《高僧傳》等資料,為早期佛經(jīng)譯寫與漢晉書法史提供了信息。在北魏以前,參與佛經(jīng)翻譯擔(dān)任“筆受”職務(wù)或者書寫抄經(jīng)者有僧人、專業(yè)寫經(jīng)生、清信士等。到了北魏時期敦煌已有官方的寫經(jīng)組織,才有“經(jīng)生”或“官經(jīng)生”的職稱。由于僧佑并未用“寫經(jīng)生”與“寫經(jīng)體”二詞,所以早期佛教經(jīng)錄中關(guān)于佛經(jīng)書寫文化的信息比較容易被忽略{2}。根據(jù)《出三藏記集》與《高僧傳》中所記載,以及現(xiàn)存5世紀(jì)以前有紀(jì)年的敦煌吐魯番遺存的佛教寫經(jīng)殘卷,寫經(jīng)所采用的書體有正書、行書、草寫與隸書[7]。由于此階段的佛經(jīng)翻譯組織與書寫文化還未定型,以下試先由竺法護譯場之書寫文化,探討初期佛經(jīng)書寫與文化交流軌跡{3}。
二 僧佑《出三藏記集》
關(guān)于佛經(jīng)書寫的記載
南朝僧佑(445—518)之著述流傳至今尚存《出三藏記集》《釋迦譜》和《弘明集》三種,其中《出三藏記集》是現(xiàn)存佛教最早的經(jīng)錄,僧佑根據(jù)道安所纂經(jīng)錄編成《出三藏記集》15卷(以下簡稱《佑錄》),詳列譯經(jīng)之原委、序文、譯經(jīng)者傳記等,也是后續(xù)隋唐編纂經(jīng)錄之依據(jù),當(dāng)中還有關(guān)于佛經(jīng)書寫字體以及書寫、抄經(jīng)的經(jīng)生等相關(guān)信息。
初期佛經(jīng)翻譯譯場組織簡單,除了主譯者,有專職負(fù)責(zé)書寫的助手,《佑錄》中記載包括筆受、手受、筆者等。筆受一職與一般寫經(jīng)生不同,不但擅長書寫,還需有深厚學(xué)養(yǎng),語言必須兼通華梵并深諳佛典義理,通過與主譯者的溝通,推敲翻譯之義理正確才能下筆[5]41-42。《佑錄》卷1云:“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zhì)文系于執(zhí)筆。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胡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后宣述經(jīng)奧于是乎正。”
另,根據(jù)《翻譯名義集》卷1所載,筆受一職始于竺法護譯場:
宋僧傳云,譯場經(jīng)館,設(shè)官分職可得聞乎,曰此務(wù)所司,先宗譯主,即赍葉書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是也。次則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xué)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后下筆。西晉偽秦已來,立此員者,即沙門道含、玄賾、姚嵩、聶承遠(yuǎn)父子。[9]
由上所述可知,自西晉以后,筆受在佛經(jīng)譯場中具有重要責(zé)任,此職從竺法護譯場中聶承遠(yuǎn)與聶道真父子開始,后有道含(竺佛念譯場)、玄賾(玄奘譯場)、姚嵩(鳩摩羅什譯場)。因佛教中的經(jīng)典、佛塔與佛像皆為傳遞佛陀圣教的載體,是佛教徒必須恭敬供養(yǎng)之法寶,所以歷代高僧對于參與經(jīng)典翻譯與譯場人員的素質(zhì)要求甚高。隋代彥琮《釋氏要覽》中提到參與佛經(jīng)翻譯人員的條件列有“八備”與“十條”:
夫預(yù)翻譯有八備、十條。一誠心受法,志在益人;二將踐勝場,先牢戒足;三文詮三藏,義貫五乘;四傍涉文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五■怉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zhí),沈于道術(shù),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六要識梵言;七不墜彼學(xué);八博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十條者: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jīng)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業(yè);九字部;十字聲。[10]
其中的“八備”主要是對個人的人品道德與學(xué)養(yǎng)之要求,首要的兩條必須是“一誠心受法,志在益人;二將踐勝場,先牢戒足”。也就是必須是誠心學(xué)法希望利益他人,并且在參與譯場前須先受戒。而后“十條”則是翻譯所需的專業(yè)語言文學(xué)能力。
三 竺法護譯場之筆受與書寫文化
(一)筆受
現(xiàn)存紀(jì)年最早的漢文佛經(jīng)殘片為西晉元康六年(296)《諸佛要集經(jīng)》殘卷,此經(jīng)是竺法護所翻譯{1},其卷尾的題記不但有明確年代,還記錄了竺法護譯場中兩位重要弟子:聶承遠(yuǎn)與竺法首,其卷后題記中有“□受聶承遠(yuǎn),和上弟子沙門竺法首筆”。聶承遠(yuǎn)與竺法首皆是竺法護譯場中的筆受,而《佑錄》中也記載,竺法首曾經(jīng)擔(dān)任兩部佛經(jīng)翻譯之筆受,包括《濟諸方等學(xué)經(jīng)》及294年于酒泉翻譯的《圣法印經(jīng)》[11]。竺法護于292年在洛陽翻譯《諸佛要集經(jīng)》時聶承遠(yuǎn)是筆受[12],吐魯番出土《諸佛要集經(jīng)》殘片的卷末題記年代顯示竺法首于296年所寫,表明此寫卷可能是在翻譯了4年之后,竺法首為流通而抄寫的復(fù)本。
竺法護翻譯佛經(jīng)約自266年開始至308年,其譯場中的助手至少有30多人[11]48。根據(jù)《佑錄》與《高僧傳》記載,擔(dān)任竺法護譯場筆受的有:清信士聶承遠(yuǎn)與聶道真父子、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竺法護傳》中提及他們都是“共承護旨執(zhí)筆詳校”的“筆受”:
時有清信士聶承遠(yuǎn),明解有才篤志務(wù)法,護公出經(jīng)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jīng)初譯,頗多煩重,承遠(yuǎn)刪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yuǎn)有子道真,亦善梵學(xué)。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zhí)筆詳校。[13]
除了上述幾位,另檢視《佑錄》所載,查考竺法護自266年至308年翻譯佛經(jīng)時筆受、手受或書寫者以及相關(guān)佛經(jīng)列表(表1)如下。
上表所列竺法護譯場中之筆受者,我們可以觀察到負(fù)責(zé)書寫的仍以漢人為主。其中聶承遠(yuǎn)參與時間最久,也是協(xié)助竺法護翻譯佛經(jīng)筆受最多的一位。竺法護譯作中比較重要的大經(jīng)也是聶承遠(yuǎn)參與合作的,例如《正法華經(jīng)》。隋代費長房也在《歷代三寶紀(jì)》提及聶承遠(yuǎn)是“執(zhí)筆助翻,卷軸最多”:
……起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懷帝世永嘉二年,其間在所遇緣便譯,經(jīng)信士聶承遠(yuǎn)執(zhí)筆助翻,卷軸最多……故知今之所獲,審是護公翻譯不疑。故聶承遠(yuǎn)子道真與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男等,前后并是筆受之人,已見別傳不復(fù)委載。[17]
由表可見,聶承遠(yuǎn)筆受至少5部佛經(jīng),其子聶道真筆受4部;竺法首雖于294年筆受《圣法印經(jīng)》(于酒泉)與《佛說濟諸方等學(xué)經(jīng)》2部,然皆僅為1卷之簡短佛經(jīng),相較之下也凸顯聶承遠(yuǎn)父子的重要性。
(二)聶承遠(yuǎn)與《正法華經(jīng)》
聶承遠(yuǎn)從266年至297年之間參與竺法護的佛經(jīng)翻譯團隊,他與竺法護的師徒情誼長達(dá)30年,如果不計其中竺法護沒有譯寫記錄的10年歲月(273—284年)[12]6-13,聶承遠(yuǎn)于286年再度參與,一直到297年為止,他實際上前后至少有20年投入竺法護的佛經(jīng)譯寫。他在參與佛經(jīng)翻譯團隊中,還培養(yǎng)自己的兒子聶道真于289年合作筆受,他們父子二人在竺法護譯場的貢獻不可小覷。以他的專業(yè)資歷,他也會教導(dǎo)他兒子寫字讀書,在團隊里也會影響其他助譯者或新進譯場之寫經(jīng)生學(xué)習(xí)書法,他對于此譯場中的書寫文化必有某種程度影響力。如果聶承遠(yuǎn)在竺法護譯場中如此舉足輕重,他所擅長的書法風(fēng)格有可能是西晉時期的官方文書的書法主流“晉書正寫”,因為根據(jù)竺法首的《諸佛要集經(jīng)》殘片的書法,學(xué)者已考證《諸佛要集經(jīng)》是典型的西晉(265—316年)官方書體“晉書正寫”[18],是公元3世紀(jì)以來佛教寫經(jīng)所用的主要書體之一[19]。當(dāng)時中原與敦煌地區(qū)主流的書法,處于漢晉“隸楷之間”的過渡階段,已是很成熟并已定型的正書。當(dāng)聶承遠(yuǎn)在292年筆受《諸佛要集經(jīng)》時,他的書法風(fēng)格,可能成為后來竺法首于296年抄寫復(fù)本所根據(jù)的一份臨寫本。那份臨寫本也許是類似目前所見的296年《諸佛要集經(jīng)》殘片的書風(fēng)。而這種正書是否是竺法護譯場中所使用的主流寫經(jīng)體,還有待考察。
《諸佛要集經(jīng)》雖然是竺法護翻譯的,但并不是竺法護譯作最知名的一部佛經(jīng)。根據(jù)《佑錄》記載,竺法護譯經(jīng)中以《光贊》《正法華》《首楞嚴(yán)》《維摩詰經(jīng)》等影響最大,尤其是《正法華經(jīng)》(于286年所譯,聶承遠(yuǎn)筆受)。初步梳理敦煌與吐魯番所出土的佛經(jīng)寫卷或殘片,據(jù)《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所錄,《正法華經(jīng)》寫本殘片遺存有:斯6728、斯2816、斯4541及敦研061{1},法藏一件編號伯4663,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北敦00065、北敦04466、北敦15713。日本《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收錄6件殘片{1},另從《吐魯番文書總目》第3冊《歐美收藏卷》收集德國收藏《正法華經(jīng)》殘片{2},初步考察有14號(表2),分別從新疆吐峪溝、勝金口與木頭溝遺址出土。
以上德國所藏的部分,若先不論屬于七八世紀(jì)以后明顯為隋唐楷書風(fēng)格殘片,有6個殘片屬于比較早期的書法風(fēng)格:Ch1788a、Ch1788b、Ch2105、Ch2531v{3}、Ch3681與Ch2821v。依其書風(fēng)可以分兩組:Ch1788a、Ch1788b、Ch2531v、Ch2821v{4}這4個殘片皆為《正法華經(jīng)》卷6《藥王如來品》(圖1—4);Ch2105與Ch3681(圖5—6)是一組為《正法華經(jīng)》卷2《應(yīng)時品》。殘片編號Ch2531v、Ch2821v、Ch1788a與Ch1788b這4個殘片之書法與竺法首《諸佛要集經(jīng)》類似,也與《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所列6件《正法華經(jīng)》殘片類似,均屬于六朝寫經(jīng)。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