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影片 《你好, 李煥英》 蘊含的孝道質(zhì)詢模式, 觸及觀眾的現(xiàn)實焦慮與道德負(fù)疚, 引發(fā)了廣泛的共情。 其敘事方式與風(fēng)格呈現(xiàn), 使觀眾在接受中通過情感宣泄實現(xiàn)自我和解。 孝道作為一種倫理要求, 其注重實踐的特點, 使影片價值導(dǎo)向偏于獲取世俗認(rèn)可, 缺乏反思和創(chuàng)造。 《你好, 李煥英》 的票房成功提示我們電影生產(chǎn)應(yīng)該注重觀眾的深層文化心理, 對其價值的反思則又提示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轉(zhuǎn)換任重而道遠(yuǎ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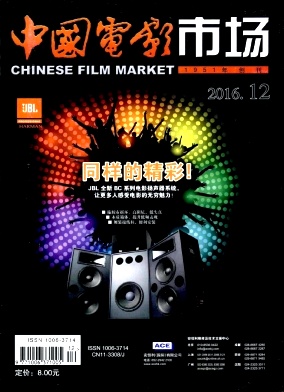
本文源自何龍, 中國電影市場 發(fā)表時間:2021-04-13《中國電影市場》(月刊)創(chuàng)刊于1951年,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主管。《中國電影市場》宣傳黨和政府關(guān)于電影發(fā)行放映的方針政策,交流國內(nèi)外電影市場信息,宣傳行業(yè)干部職工先進(jìn)人物先進(jìn)事跡,交流業(yè)務(wù)、技術(shù)經(jīng)驗。《中國電影市場》被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收錄。
【關(guān)鍵詞】 孝道 《你好, 李煥英》 賈玲 春節(jié)檔
《你好, 李煥英》 顯然是今年最強(qiáng)春節(jié)檔的一匹黑馬, 影片以 52 億元拿下中國電影票房亞軍, 并躋身世界電影票房百強(qiáng), 成為一部現(xiàn)象級作品。那么 《你好, 李煥英》 的票房奇跡是如何締造的呢?
從外部環(huán)境上, 時勢造就了今年的 “史上最強(qiáng)春節(jié)檔”。 其一, 這是后疫情時期中國人就地過年的第一個春節(jié), 看電影成為春節(jié)新民俗。 還在疫情期間, 就地過年讓許多人遠(yuǎn)離 “家” 的環(huán)境, 能夠進(jìn)行的活動并不多, 看電影成為必選項之一。 其二, 今年的電影宣發(fā)迎來大變局。 “借著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的東風(fēng), 電影營銷范式得到了再一次進(jìn)化”。 [1] 以上兩點是 《你好, 李煥英》 票房成功的外部原因。 從內(nèi)在角度, 《你好, 李煥英》 母女親情的主題, 非常適合春節(jié)期間的家庭觀影, 相比競爭對手, 在題材上更勝一籌。 這部電影根據(jù)小品改編, 同名小品曾在 2016 年浙江衛(wèi)視 《喜劇總動員》上演, 積累了一定的人氣。
然而以上都不足以解釋 《你好, 李煥英》 的票房奇跡, 筆者以為, 影片以獨特的中國情感表達(dá)契合了特定時期的觀眾心理, 是其票房成功的關(guān)鍵。
一、 情感內(nèi)核: 傳統(tǒng) “孝道” 的質(zhì)詢
《你好, 李煥英》 根據(jù)賈玲的親身經(jīng)歷改編而成。 故事講述了母親意外去世, 主人公賈曉玲認(rèn)為自己沒有做過一件讓母親李煥英高興的事情, 自己的到來只是給母親帶來了無盡的麻煩, 甚至認(rèn)為若非自己的出生, 母親會更幸福。 “樹欲靜而風(fēng)不止, 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 賈曉玲抱著這樣一種負(fù)疚感, 穿越到李煥英年輕的八零年代。 影片以女兒的視角, 試圖去彌補(bǔ)對母親的 “未盡之孝”。
《爾雅·釋訓(xùn)》 有言: “善事父母為孝。” 如果說親情是一種人類共同的情感, “孝道” 則是建立在親情基礎(chǔ)上的倫理要求。 “孝” 作為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中最核心的一環(huán), 有著層次豐富的意義: 從最基本的 “身體發(fā)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 《孝經(jīng)》 ) 到 “揚名于后世, 以顯父母” ( 《孝經(jīng)》 ),孝道倫理涵括了中國人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
家族競爭是中國式孝道存在的一大背景。 個人其實是鏈條中的一環(huán), 其價值被放在一個比個人更大的背景中去考量。 個人的使命, 并不是 “做自己”, 而是出人頭地, 成為家族鏈條中強(qiáng)有力的一環(huán)。 這種情況在今天并未改變, 孝道被簡化為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掙更多的錢, 出更大的名, 表現(xiàn)在影片中, 即是 “長臉” ( “以顯父母” 的當(dāng)代表現(xiàn))。
想一想坐在電影院里就地過年的都市白領(lǐng)和各式各樣的打工人, 在這個本該回到父母身邊去接受各種關(guān)心和盤問的春節(jié), 無論他們從事什么職業(yè), 有著怎樣的都市身份, 此刻都秒變 “二蛋” “二狗”。 觀眾跟隨賈曉玲, 換一種方式來到母親的身邊, 他們身上潛藏的 “ 孝道” 質(zhì)詢模式被啟動, 在影片混合著淚與笑的催化下, 一種前所未有的共情將他們籠罩。
有家長批評影片的教育觀, 認(rèn)為好的教育是讓孩子自由成長, 讓他們永遠(yuǎn)不要對父母懷有愧疚之心。 有評論家批評這部電影 “可以說是一種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價值觀” [2] 。 甚至 “無論是母親對于孩子的期待, 還是孩子對于母親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判斷, 其內(nèi)核是非常一致的, 都是當(dāng)代的成功學(xué)” [3] 。 但大部分觀眾被電影深深感動, 正如中紀(jì)委網(wǎng)站稱贊這部影片 “用溫情而真摯的藝術(shù)手法顯現(xiàn)了細(xì)膩、 無私的母愛, 感動了無數(shù)人的心” [4] 。
如何看待這些針鋒相對的觀影感受? 讓我們回到影片本身。 賈曉玲其實是在母親的影響下 (也是在現(xiàn)實的要求下) 成長的, 她的目標(biāo)被設(shè)定為在名利上超越他人, 即 “長臉”。 這當(dāng)然是淺薄的價值觀, 卻也是當(dāng)下人們普遍認(rèn)同的價值觀。 修復(fù)賈曉玲對母親的愧疚之情的, 依舊是通過實現(xiàn)這一切, 來對母親進(jìn)行告慰。 在影片結(jié)尾, 功成名就的賈曉玲開著敞篷車在盤山公路上驅(qū)馳, 她幻想母親身著名貴大衣, 與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悅。 而母親呢? 影片一再重復(fù)的, 是對孩子無私的愛 (希望孩子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這種對孩子平凡樸實的愛, 與現(xiàn)實是脫節(jié)的, 影片一開始, 我們看到父母為女兒操辦升學(xué)宴時志得意滿的驕傲、 實實在在的 “長臉”。
觀眾和評論家所看到的影片價值觀的裂縫, 也是我們在生活中確確實實遭遇的困境。 比如現(xiàn)在的家長在孩子很小的時候, 給他報各種興趣班, 而一到小學(xué)高年級, 便把各種興趣班砍掉, 專攻語數(shù)外。 在孩子小的時候, 他們相信教育是發(fā)掘孩子的興趣, 讓孩子自由成長, 而一旦面臨 “擇校”, 他們會立刻加入 “教育軍備賽”, 成為虎媽虎爸。 家長們其實是在兩種教育觀之間切換。 同樣, 現(xiàn)實生活中的父母對子女無私付出, 有著平凡樸實的愛, 也并不代表父母沒有壓力、 沒有焦慮, 這些壓力和焦慮同樣會傳導(dǎo)至下一代, 并塑造他們。
這正是中國當(dāng)下的普遍現(xiàn)實, 觀眾對電影中雖然淺顯卻真實的母女關(guān)系產(chǎn)生了深切的認(rèn)同。 從這一角度他們認(rèn)定這部影片是真實的、 接地氣的。 與賈曉玲一樣, 觀眾心中的不解之結(jié)正是自己努力生活和工作, 還是無法滿足父母的世俗期待。 孝不僅僅是藏在心里的情感, 更需要作為一種行動, 實現(xiàn)在現(xiàn)實人生中。 大部分人在這種價值觀的衡量下, 不免產(chǎn)生一種巨大的負(fù)疚感。 包括賈玲, 這位成功超越絕大多數(shù)國人的當(dāng)紅演員、 導(dǎo)演, 她的遺憾是母親無法見證這一切。 [5] 這是國人心中永遠(yuǎn)的情結(jié), 每一位觀眾, 在春節(jié)這個注重家庭、 注重傳統(tǒng)的節(jié)點, 在黑暗的影廳里接受一次 “孝道” 的質(zhì)詢, 讓他們埋藏心底的負(fù)疚感能夠被討論、 被觸碰。 《你好, 李煥英》 的票房奇跡, 正是中國式情感在特定時空的一次大爆發(fā)。
二、 故事與風(fēng)格: 修復(fù)、 宣泄與和解
賈曉玲帶著負(fù)疚感穿越到一九八一年, 去彌補(bǔ)未盡之孝, 讓李煥英高興一回。 所過之處, 影像由黑白變回彩色, 一個逝去的時代失而復(fù)得。 賈曉玲以表妹身份與年輕的李煥英相處, 開始幫她改變命運: 第一個買電視、 組織參加女排比賽, 與廠長兒子沈光林相親。 這是影片的主體部分, 在小品演員賈玲的掌控下, 笑點不斷, 一種輕松的懷舊之感讓觀眾得以從現(xiàn)實中抽離。
然而李煥英已經(jīng)與賈文田結(jié)婚, 賈曉玲的一切努力皆告失敗, 影片在情緒上陷入低谷。 就在賈曉玲想結(jié)束這一切時, 她有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 原來母親也是穿越回來的。 頓悟真相的賈曉玲一路淚奔一路狂奔, 影片以系列閃回補(bǔ)敘母親配合自己完成 “未盡之孝” 的種種細(xì)節(jié)。 賈曉玲摔倒, 影片突然給了主人公全知視角。 一系列母親陪女兒成長的細(xì)節(jié), 以并不高明的蒙太奇疊化剪接。 母女二人終于見面, 相擁而泣。
這個反轉(zhuǎn)將之前的喜劇氣息完全推倒, 母親隱忍無私的形象得以確立。 與現(xiàn)實中世故的母親相反, 這個母親對女兒一無所求, 只留下 “一把屎一把尿?qū)⒑⒆永洞?rdquo; 的形象。 觀眾與主人公一起, 在無私母愛中, 對孝道質(zhì)詢下的負(fù)疚感進(jìn)行修復(fù)。正如評論者所言: “無論我們多么糟糕和狼狽, 在父母眼里永遠(yuǎn)只有無條件的包容與疼愛, 甚至可以配合我們的孝心去演繹一場自我感動的戲碼, 為的只是讓我們獲得心安。” [6] 奔跑著哭泣著的賈曉玲所宣泄的 “自我感動” 同樣也是觀眾的。 這一刻, 觀眾與主人公一起, 確認(rèn)了來自母親的原諒。 負(fù)疚感在宣泄中被療愈, 觀眾實現(xiàn)了與自我的和解。
從這個角度看, 母親的形象其實是根據(jù)女兒的需求塑造的, 她在歷史時空中的復(fù)雜處境與感受, 并不為作者所關(guān)心。 “她進(jìn)廠時是一個光榮的社會主義工人, 去世前即使工廠不破產(chǎn)轉(zhuǎn)型、 工人不下崗, 境況也可能蒼涼。 中間這三十年, 她經(jīng)歷過什么? 心情是怎么樣的?” [7] 歷史的背景被簡化為一塊幕布, 提供一個親情戲碼展開的場景而已。 至于對年輕母親最重要的細(xì)節(jié)———與父親羅文田婚戀, 則付諸闕如。
由此再回到前面談及的價值觀問題, 便會豁然而解。 世俗標(biāo)準(zhǔn)的考核無處不在 (在春節(jié)期間更甚), 對于生活在高度競爭化的當(dāng)下的年輕人們, “孝道” 的質(zhì)詢顯然戳中了他們的精神痛點。 而影片以悲喜交集、 由笑而淚的方式, 使他們在情緒上獲得宣泄, 得以平復(fù)。 這難道不是一份給年輕人特殊的春節(jié)禮物嗎?
三、 市場啟示與價值反思
《你好, 李煥英》 的票房成功給我們特別的啟示。
其一, 在新的歷史時期, 講述中國故事, 抒發(fā)中國情感, 有著巨大的票房潛力。 而講述中國故事, 抒發(fā)中國情感, 不能忽視對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盡管電影藝術(shù)是舶來品, 在一百多年的實踐中, 電影的民族化卻取得了巨大成就。 電影市場與文化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 也早已為影史所印證。
重視文化傳統(tǒng), 首先體現(xiàn)在思想情感的表達(dá)與文化心理的反映。 《你好, 李煥英》 以 “孝道” 為主題, 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 同樣獲得票房的巨大成功。這讓我們想起默片時代的 《神女》, 以及八九十年代家喻戶曉的 《媽媽再愛我一次》 (觀影人數(shù)超 2 億)。 可見繼承文化傳統(tǒng), 展現(xiàn)中國人深層文化心理的影片能夠跨越時代, 屢創(chuàng)票房奇跡。
重視文化傳統(tǒng), 還體現(xiàn)在電影敘事和審美上。一度我們以為商業(yè)電影就必須是好萊塢的敘事模式, 劇本在第幾頁應(yīng)該有副線、 有反轉(zhuǎn), 都有固定的框架模式, 這才是工業(yè)化的娛樂電影。 而現(xiàn)實正如專家所言: “春節(jié)檔電影與好萊塢主流電影敘事拉開了距離, 敘事模式、 節(jié)奏均不同于好萊塢電影。” [8] 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 孕育了不同的電影形式和審美偏好。 市場的正向反饋提示電影人應(yīng)注重對文化傳統(tǒng)進(jìn)行轉(zhuǎn)換與創(chuàng)造。
其二, 在藝術(shù)實踐中對文化傳統(tǒng)進(jìn)行傳承與轉(zhuǎn)換,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或許正是 《你好, 李煥英》 在思想深度上的某些妥協(xié), 使之兼容了更大的觀眾群和更普遍的共情, 人們在觀影中得以宣泄自己的情感, 這種宣泄締造了票房奇跡, 卻也是以犧牲作品的深度為代價的。 這就注定 《你好, 李煥英》 不會成為經(jīng)典, 因其無法在思想上給觀眾以新的養(yǎng)分。
孝道只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主流價值觀的傳導(dǎo)器, 因為孝道衡量成敗與否, 使用的正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標(biāo)準(zhǔn)。 只能說, 這是一個成功學(xué)、 消費主義主導(dǎo)的時代。 在孝道的考核機(jī)制下, 人們偏向于認(rèn)同和實踐當(dāng)下的世俗價值, 很少去質(zhì)疑、 反思和創(chuàng)造。 孝道作為一種倫理要求, 其注重實踐的特點, 使其價值導(dǎo)向偏于獲取世俗認(rèn)可。
不可否認(rèn), 《你好, 李煥英》 在敘事與風(fēng)格上的獨特呈現(xiàn), 為傳統(tǒng)孝道注入了自由、 平等的新內(nèi)容。 通過穿越的敘事方式, 影片呈現(xiàn)了李煥英與賈曉玲之間母女/ 姐妹的雙重關(guān)系, 將朋友、 閨蜜式的自由、 平等精神注入母女關(guān)系中。 這或許是影片獲得廣泛共情的另一個原因。 傳統(tǒng)孝道的新發(fā)展, 使其刻板形象得以改觀, 更能為當(dāng)下觀眾所認(rèn)同。
然而, 傳統(tǒng)孝道如何融合現(xiàn)代個體精神向度的需求呢? 史鐵生的 《我與地壇》 與影片 《 你好, 李煥英》 有著共同的預(yù)設(shè)情境。 知青史鐵生年紀(jì)輕輕癱瘓在輪椅上, 母親焦灼不已, 為兒子奔走, 直至離世, 沒能看到兒子的成名。 當(dāng)觀眾在觀看電影《你好, 李煥英》 時, 他獲得的和解是即時的, 酣暢然而短暫, 經(jīng)不起時間的考驗; 而讀者在 《我與地壇》 中獲得的力量卻深沉而持久, 足以幫助他們直面命運。 拿一部當(dāng)下的電影與一部載入史冊的文學(xué)經(jīng)典作比, 當(dāng)然是一種苛求。 筆者只是想借此想象一下, 在講述中國故事、 抒發(fā)中國情感的大道上, 還有許多領(lǐng)地需要我們的電影人去開拓。 而《你好, 李煥英》, 顯然開了一個好頭。
結(jié)語
筆者以為, 影片 《你好, 李煥英》 締造票房奇跡的內(nèi)在原因, 是其蘊含的孝道質(zhì)詢模式, 在特定時空 (后疫情春節(jié)檔), 觸及了觀眾的現(xiàn)實焦慮與道德負(fù)疚, 因而引發(fā)了廣泛共情。 而賈玲在敘事與風(fēng)格上的精準(zhǔn)把握, 滿足了廣大觀眾通過情感宣泄實現(xiàn)自我和解的消費心理。 《你好, 李煥英》 的票房成功提示我們電影生產(chǎn)應(yīng)該注重觀眾的深層文化心理, 對其價值的反思則又提示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轉(zhuǎn)換任重而道遠(yuǎn)。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