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杰弗里的《不列顛君王史》、瓦斯的《布魯特傳奇》和拉亞蒙的《布魯特》,特別是它們的亞瑟王部分,代表中世紀(jì)盛期英國(guó)不列頓、盎格魯-諾曼和盎格魯-薩克遜三個(gè)主要文化傳統(tǒng)并反映出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復(fù)雜的社會(huì)、政治和文化生態(tài)。拉亞蒙使用英格蘭普通民眾的語(yǔ)言、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tǒng)和古英語(yǔ)頭韻體史詩(shī)風(fēng)格改寫(xiě)瓦斯代表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政治利益和主流宮廷文化的盎格魯-諾曼語(yǔ)詩(shī)作,并且同杰弗里的拉丁編年史互文,將亞瑟王塑造成英格蘭英雄和君主,其明顯的英格蘭性表達(dá)出英格蘭人的民族立場(chǎng)和文化傳承,也預(yù)示著英國(guó)文化未來(lái)的建構(gòu)與發(f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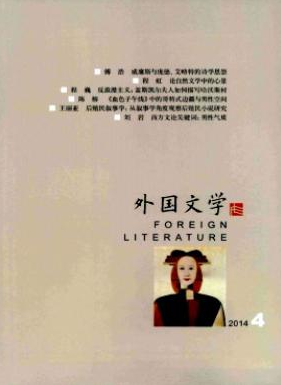
肖明翰, 外國(guó)文學(xué)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9-22
關(guān)鍵詞:拉亞蒙 《布魯特》 《布魯特傳奇》 《不列顛君王史》 英格蘭性
在 12 世紀(jì),英國(guó)出現(xiàn)了三部?jī)?nèi)在關(guān)聯(lián)密切且具有特殊意義的不列顛編年史:不列頓人后裔威爾士學(xué)者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 1100?—1155)的《不列顛君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1136?)、盎格魯-諾曼詩(shī)人瓦斯(Robert Wace, 1110?— 1174?)的《布魯特傳奇》(Le Roman de Brut, 1155)和盎格魯-薩克遜詩(shī)人拉亞蒙(Layamon, 生卒年不詳)的《布魯特》(Brut, 12 世紀(jì)末)。說(shuō)它們關(guān)系密切,是因?yàn)橥咚沟摹恫剪斕貍髌妗肥怯冒桓耵?諾曼語(yǔ)(在英格蘭使用的法語(yǔ),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官方語(yǔ)言)對(duì)杰弗里的拉丁散文著作的詩(shī)體翻譯和改寫(xiě),而拉亞蒙的《布魯特》則是對(duì)瓦斯詩(shī)作的中古英語(yǔ)詩(shī)體的翻譯和改寫(xiě)。因此,它們的基本內(nèi)容大體相同,都是以傳說(shuō)中特洛伊幸存者羅馬創(chuàng)建人埃涅阿斯的曾孫布魯特創(chuàng)建不列顛開(kāi)篇,敘述了公元 682 年最后一個(gè)不列頓王國(guó)滅亡前共 99 位大多為傳說(shuō)中的不列頓國(guó)王的“歷史”。
至于說(shuō)它們具有特殊意義,則是因?yàn)檫@三部著作分別植根于中世紀(jì)盛期英國(guó)三個(gè)主要文化傳統(tǒng)——威爾士人的不列頓傳統(tǒng)、盎格魯-諾曼王朝的宮廷文化傳統(tǒng)和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日耳曼或者說(shuō)已本土化了的英格蘭傳統(tǒng),并代表不列頓人、盎格魯-諾曼人和盎格魯-薩克遜人三大民族的意識(shí)形態(tài)、政治態(tài)度和文化立場(chǎng)。這三部著作和它們的互文反映了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的社會(huì)、政治和文化生態(tài)并預(yù)示英國(guó)文化和英格蘭民族未來(lái)的發(fā)展。這些都直接或間接但都特別突出地表現(xiàn)在拉亞蒙這位后來(lái)者的詩(shī)作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當(dāng)時(shí)的英國(guó),英格蘭人(the English)是指盎格魯-撒克遜人;所以英格蘭性(Englishness)主要指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意識(shí)。
這三部著作中內(nèi)容最豐富也最有影響的都是其中的亞瑟王部分,它是三位作者編導(dǎo)的不列顛歷史大劇的高潮,而瓦斯和拉亞蒙在翻譯和改寫(xiě)各自的源本時(shí)都對(duì)這部分著力最勤;因此這部分篇幅大幅度增加,從杰弗里編年史里稍多于四分之一增加到拉亞蒙詩(shī)作里超過(guò)三分之一。這些著作里的亞瑟王敘事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了后來(lái)風(fēng)靡歐洲多得難以計(jì)數(shù)的亞瑟王傳奇作品,特別是其中那些王朝主題著作從框架到基本內(nèi)容大都取材于此。同時(shí),亞瑟王部分最明顯地表現(xiàn)出三位作者的思想意識(shí)和民族心理。其中,拉亞蒙在他的敘事里,在他對(duì)瓦斯的改寫(xiě)以及同杰弗里的互文中,a 特別明顯地表達(dá)出他的民族立場(chǎng)和文化傳承。
在英格蘭文化史和英語(yǔ)文學(xué)史上,拉亞蒙的《布魯特》在許多方面都是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它是《盎格魯-薩克遜編年史》b 終止后第一部英語(yǔ)編年史體裁著作;它長(zhǎng)達(dá) 16,096 行,是中古英語(yǔ)第一部長(zhǎng)篇敘事詩(shī),也是喬叟時(shí)代英語(yǔ)文學(xué)繁榮之前最長(zhǎng)的英語(yǔ)詩(shī)作;它是古英詩(shī)歷史終結(jié)后第一部英語(yǔ)頭韻體長(zhǎng)篇,因此也是后來(lái)成就輝煌的頭韻體復(fù)興運(yùn)動(dòng)的源頭;它還是諾曼征服后第一部從風(fēng)格到精神實(shí)質(zhì)都繼承和發(fā)展古英語(yǔ)史詩(shī)傳統(tǒng)并在新的歷史語(yǔ)境中表達(dá)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意識(shí)的作品;當(dāng)然它關(guān)于亞瑟王朝的部分也是英語(yǔ)亞瑟王文學(xué)的開(kāi)山之作。這些表明《布魯特》在英語(yǔ)文學(xué)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反映出它特殊的歷史文化意義和拉亞蒙在諾曼征服后英語(yǔ)語(yǔ)言和英格蘭文化文學(xué)最低潮時(shí)期對(duì)英格蘭傳統(tǒng)的堅(jiān)持。
拉亞蒙堅(jiān)持英格蘭傳統(tǒng)最明顯的表現(xiàn)也是《布魯特》最突出的特征。是當(dāng)法語(yǔ)詩(shī)歌正風(fēng)靡歐陸和英國(guó)、源自法語(yǔ)詩(shī)傳統(tǒng)的節(jié)律體在敘事詩(shī)中大行其道之時(shí),甚至他手中的源本瓦斯的《布魯特傳奇》使用的也是該詩(shī)體,他卻逆潮流不僅使用被社會(huì)上層和文化界所不屑的下層民眾的英語(yǔ),而且還使用在諾曼征服后早已在主流文學(xué)界銷(xiāo)聲匿跡的古英詩(shī)頭韻體。《布魯特》表明,他似乎是在竭力“復(fù)古”。他除使用古英詩(shī)頭韻體外,還大量甚至盡量使用古英語(yǔ)詞匯。盧米斯(Roger Sherman Loomis)指出:“任何一個(gè)讀過(guò)比較多最早的英語(yǔ)詩(shī)歌的人都不會(huì)對(duì)拉亞蒙感到陌生……其詞匯絕大多數(shù)來(lái)自薩克遜語(yǔ),僅有 150 個(gè)羅曼語(yǔ)詞匯”(110)。另外,拉亞蒙還在詩(shī)作中大量使用同義詞和復(fù)合詞。任何熟悉古英詩(shī)的人都知道,出于押頭韻、便于演唱時(shí)記憶和避免用詞重復(fù)呆板等方面的需要,古英詩(shī)一個(gè)特別突出的特征就是同義詞極為豐富并大量使用復(fù)合詞。所以,拉亞蒙詩(shī)作里“明顯有意識(shí)的復(fù)古傾向在各語(yǔ)言層次上都表現(xiàn)出來(lái),比如他詩(shī)歌的遣詞造句和詞匯構(gòu)成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更古老的英雄詩(shī)歌的回響”(Elsweiler 2)。
拉亞蒙作品中的“復(fù)古”傾向基本上是學(xué)界共識(shí),但也有學(xué)者指出,詩(shī)人受他所處時(shí)代的語(yǔ)言和文學(xué)潮流影響,也使用了許多“他那個(gè)時(shí)代的 [英語(yǔ)] 日常詞匯 a” (Roberts 113)。另外,他很少使用古英詩(shī)里極為普遍的“復(fù)合詞隱喻”(kenning),卻較多使用源自拉丁和法語(yǔ)詩(shī)歌的明喻(simile)。他詩(shī)行的頭韻也并非像古英詩(shī)那樣嚴(yán)格,而且他在系統(tǒng)使用頭韻的同時(shí)還比較普遍使用源自法語(yǔ)節(jié)律體的尾韻。當(dāng)然這些特征并不否定拉亞蒙對(duì)古英詩(shī)傳統(tǒng)十分明顯的繼承。他是在新的社會(huì)、語(yǔ)言和文化文學(xué)語(yǔ)境中創(chuàng)作,因此很自然地將新的語(yǔ)言和文化因素吸納進(jìn)詩(shī)作。這些新因素表明他詩(shī)作的開(kāi)放性并預(yù)示英詩(shī)未來(lái)的發(fā)展,也說(shuō)明他的創(chuàng)作在本質(zhì)上不是真的“復(fù)古”,而是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與未來(lái)。
但問(wèn)題是拉亞蒙為什么要逆潮流為他嘔心瀝血撰寫(xiě)的鴻篇巨制選擇似乎早已“過(guò)時(shí)”的古英語(yǔ)和古英詩(shī)頭韻體,而不用他不僅熟練掌握而且與宗教和政治權(quán)力、與主流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拉丁或盎格魯-諾曼語(yǔ)以及當(dāng)時(shí)正廣泛流行的浪漫傳奇詩(shī)體,它們?cè)诋?dāng)時(shí)不僅更權(quán)威,而且在社會(huì)上層和知識(shí)界擁有更廣泛受眾,自然也更為時(shí)髦。拉亞蒙的選擇有深刻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根源和他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因素。在諾曼征服后相當(dāng)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英國(guó)沒(méi)有形成統(tǒng)一的民族。外來(lái)的諾曼王室和貴族特別是其上層直到 14 世紀(jì)還在竭力使用自己的語(yǔ)言、遵循自己的風(fēng)俗習(xí)慣和維護(hù)源自大陸的宮廷文化,他們竭力與他們所征服和統(tǒng)治的民眾保持相當(dāng)距離,也就是說(shuō)他們還沒(méi)有真正本土化或者說(shuō)英格蘭化。所以,以盎格魯-薩克遜人為主體的英國(guó)廣大民眾與盎格魯-諾曼王室和上層貴族之間還沒(méi)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認(rèn)同和民族身份。不僅如此,由于政治權(quán)力和經(jīng)濟(jì)利益上的沖突,英格蘭民眾與統(tǒng)治階層之間不時(shí)處于緊張關(guān)系之中。學(xué)者們發(fā)現(xiàn),在 11、12 世紀(jì),在盎格魯-薩克遜貴族早已被系統(tǒng)消滅之后,當(dāng)時(shí)的年鑒中還有關(guān)于“整個(gè)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試圖反叛的記載(Thierry 362)。到 12 世紀(jì)末和 13 世紀(jì)前期,即拉亞蒙生活的時(shí)代,盎格魯-諾曼王朝的統(tǒng)治在一些地區(qū)仍然遭到英格蘭人抵制,而諾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包括古英語(yǔ)詩(shī)歌,仍然在那些地區(qū)流行。當(dāng)時(shí)流傳下來(lái)的一些文本中表現(xiàn)出“反諾曼的情緒”(antiNorman feeling)。另外,古英語(yǔ)文本仍然在一些地區(qū)傳抄;特別是在中部地區(qū)的西部(West Midland),人們熱衷于保存英語(yǔ)文獻(xiàn),甚至形成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復(fù)興運(yùn)動(dòng)。而拉亞蒙所在的伍斯特郡就在那一地區(qū),因此“拉亞蒙非常有可能受到他所處地區(qū)那很明顯的盎格魯-薩克遜復(fù)興運(yùn)動(dòng)的影響”(Knight 81)。其實(shí),伍斯特地區(qū)一直有維護(hù)和保存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傳統(tǒng)。諾曼征服后,伍斯特的武甫斯坦主教 a 一直堅(jiān)持維護(hù)并在其布道詞中表達(dá)盎格魯-薩克遜時(shí)代的傳統(tǒng)和宗教文化。因此,作為薩克遜人后裔和生活在那一地區(qū)的神甫,拉亞蒙受當(dāng)?shù)匕桓耵?薩克遜或者說(shuō)英格蘭文化復(fù)興運(yùn)動(dòng)的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實(shí)際上,《布魯特》那“古舊的(archaic)語(yǔ)言特征可以被理解為拉亞蒙有意保存或復(fù)活盎格魯-薩克遜文學(xué)傳統(tǒng)的一種嘗試”(Elsweiler 369)。也就是說(shuō),他使用古英語(yǔ)特征的詩(shī)歌語(yǔ)言具有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方面的現(xiàn)實(shí)意義。阿隆斯坦(Susan Aronstein)認(rèn)為,拉亞蒙的《布魯特》“反映當(dāng)時(shí)正在增長(zhǎng)的英格蘭性”(38)。所以嚴(yán)格地說(shuō),拉亞蒙并非真要復(fù)古,而是在新的社會(huì)和文化語(yǔ)境中表達(dá)和發(fā)揚(yáng)他所繼承的英格蘭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以應(yīng)對(duì)當(dāng)時(shí)代表諾曼征服者利益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官方文化體系。因此,拉亞蒙吸取新的語(yǔ)言材料和詩(shī)歌風(fēng)格表明他并沒(méi)有脫離現(xiàn)實(shí),而他使用古英語(yǔ)詞匯和古英詩(shī)風(fēng)格則體現(xiàn)他的文化身份和政治立場(chǎng)。這兩方面在他詩(shī)作中相輔相成,并推進(jìn)了英格蘭性的發(fā)展。其實(shí),拉亞蒙不僅僅是受盎格魯-薩克遜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影響,他的《布魯特》本身就是這一運(yùn)動(dòng)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它最重要、最優(yōu)秀的成果。
任何時(shí)代,被征服民族堅(jiān)持使用本族語(yǔ)言一般都具有政治、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意義,中世紀(jì)也不例外。在中世紀(jì)歐洲,特別是在不列顛群島,由于異族頻繁入侵強(qiáng)行推行其政治權(quán)力、意識(shí)形態(tài)、文化和語(yǔ)言,因而造成不同民族之間很復(fù)雜的沖突局面。在這樣的生態(tài)中,作為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之體現(xiàn)的語(yǔ)言往往成為斗爭(zhēng)焦點(diǎn)。米德?tīng)栴D(Anne Middleton)認(rèn)為:“中世紀(jì)研究的一個(gè)核心問(wèn)題是對(duì)權(quán)威文本進(jìn)行本土語(yǔ)言化的轉(zhuǎn)化過(guò)程,并藉此對(duì)權(quán)威加以重新界定”。在 12 世紀(jì)的英國(guó),權(quán)威文本使用拉丁和盎格魯-諾曼語(yǔ),而拉亞蒙的《布魯特》正是對(duì)杰弗里的拉丁和瓦斯的盎格魯-諾曼語(yǔ)權(quán)威文本“進(jìn)行本土語(yǔ)言化的轉(zhuǎn)化”(30)。
英格蘭特殊的歷史語(yǔ)境及其文化和語(yǔ)言的發(fā)展特別能支持米德?tīng)栴D的觀點(diǎn)。在中世紀(jì),英格蘭頻遭外族入侵,形成十分復(fù)雜的語(yǔ)言和文化局面。特別是諾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及其追隨者們運(yùn)用他們?cè)诤谒雇⑺箲?zhàn)場(chǎng)上以及在隨后系統(tǒng)消滅盎格魯-薩克遜貴族的平叛中獲得的不可爭(zhēng)辯的政治權(quán)力,首先用拉丁語(yǔ)逐漸取代英語(yǔ)的官方和書(shū)面語(yǔ)地位,隨后盎格魯-諾曼王朝又用統(tǒng)治階級(jí)自己的母語(yǔ)諾曼底法語(yǔ)作為官方語(yǔ)言。于是英格蘭出現(xiàn)教會(huì)和學(xué)術(shù)界使用拉丁語(yǔ),統(tǒng)治階級(jí)和政府使用盎格魯-諾曼語(yǔ),而普通民眾主要使用英語(yǔ)、威爾士語(yǔ)以及斯堪的納維亞語(yǔ)的復(fù)雜局面。在諾曼征服之前,英語(yǔ)曾輝煌四個(gè)多世紀(jì),是當(dāng)時(shí)歐洲唯一的書(shū)面和官方民族語(yǔ)言,它獨(dú)步歐洲民族語(yǔ)文壇,創(chuàng)作出那時(shí)期歐洲唯一高度發(fā)展的民族語(yǔ)言文學(xué),產(chǎn)生了《貝奧武甫》《十字架之夢(mèng)》《流浪者》等一系列永遠(yuǎn)令英格蘭人驕傲的文學(xué)杰作。然而諾曼征服后,隨著英格蘭人被征服,英語(yǔ)降格為中下層民眾的口語(yǔ),古英語(yǔ)文學(xué)的輝煌也成為過(guò)去。
所以,拉亞蒙并非僅僅用“古舊”的英語(yǔ)和頭韻體古英詩(shī)風(fēng)格翻譯瓦斯的《布魯特傳奇》,在更廣泛同時(shí)也更深層的意義上,他是在用曾經(jīng)長(zhǎng)期輝煌的英格蘭本土文化、古英詩(shī)傳統(tǒng)和他自己的思想意識(shí)對(duì)體現(xiàn)當(dāng)時(shí)在英國(guó)占主導(dǎo)地位的盎格魯-諾曼文化的瓦斯源本進(jìn)行改寫(xiě)。使用諾曼底法語(yǔ)的詩(shī)人瓦斯屬于盎格魯-諾曼王朝統(tǒng)治下的安茹帝國(guó)之主流文化,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正在興起的宮廷文化的價(jià)值觀念和宮廷文學(xué)的體裁風(fēng)格對(duì)杰弗里的拉丁《不列顛君王史》進(jìn)行翻譯和改寫(xiě)。他將《布魯特傳奇》獻(xiàn)給當(dāng)時(shí)歐洲主流宮廷文化文學(xué)引領(lǐng)者亨利二世的王后艾琳諾,頗受贊賞。亨利二世隨即吩咐他撰寫(xiě)諾曼王朝的“歷史”,可見(jiàn)瓦斯對(duì)杰弗里文本的改寫(xiě)得到了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政治權(quán)力中心和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認(rèn)可。
如果說(shuō)瓦斯是正在興起的宮廷文化和文學(xué)潮流的代表詩(shī)人的話,那么拉亞蒙顯然是已經(jīng)延續(xù)和發(fā)展了五個(gè)多世紀(jì)并產(chǎn)生出豐碩成果的英格蘭本土文化和文學(xué)傳統(tǒng)在當(dāng)時(shí)最重要的傳人。如弗萊契(Robert Huntington Fletcher)所說(shuō):“瓦斯是一位中世紀(jì)法語(yǔ)宮廷詩(shī)人;拉亞蒙則是《貝奧武甫》的作者和那位撰寫(xiě)關(guān)于埃塞爾斯坦大勝之頌詩(shī) a 的詩(shī)人之后裔”(156)。因此,拉亞蒙不可避免地會(huì)用他所繼承的英格蘭文化和文學(xué)傳統(tǒng)對(duì)他所“翻譯”的瓦斯詩(shī)作進(jìn)行改寫(xiě)。通過(guò)比較他的《布魯特》和瓦斯的《布魯特傳奇》,我們可以看出,拉亞蒙不僅繼承了古英語(yǔ)詩(shī)歌傳統(tǒng),而且還繼承了古英語(yǔ)詩(shī)人們運(yùn)用在盎格魯-薩克遜社會(huì)仍然保持強(qiáng)大影響的日耳曼傳統(tǒng)改寫(xiě)包括《舊約》故事在內(nèi)的拉丁權(quán)威文本的傳統(tǒng)。古英語(yǔ)詩(shī)人改寫(xiě)《舊約》故事而成的詩(shī)篇占現(xiàn)存全部古英詩(shī)篇幅約三分之一,是古英語(yǔ)文學(xué)特別重要的部分。在這些被稱(chēng)為“《舊約》詩(shī)篇” 的古英詩(shī)里,詩(shī)人們從描寫(xiě)細(xì)節(jié)、情節(jié)安排、人物塑造甚至主題思想等各方面都有意識(shí)或無(wú)意識(shí)地根據(jù)他們繼承的日耳曼價(jià)值觀念和頭韻體詩(shī)歌藝術(shù)對(duì)《舊約》故事做了程度不同的改寫(xiě),取得很高的文學(xué)成就,也促進(jìn)了基督教和日耳曼兩大文化傳統(tǒng)的融合和英格蘭文化的發(fā)展。a 拉亞蒙承繼這一傳統(tǒng),運(yùn)用古英語(yǔ)前輩詩(shī)人改寫(xiě)《舊約》文本的方式,對(duì)瓦斯那部服務(wù)于盎格魯-諾曼王朝政治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布魯特傳奇》進(jìn)行改寫(xiě),很好地實(shí)現(xiàn)了他在 12 世紀(jì)后期的歷史語(yǔ)境中繼承和發(fā)展英格蘭文化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意圖。拉亞蒙的改寫(xiě)也包括細(xì)節(jié)描寫(xiě)、情節(jié)敘述和人物塑造等許多方面;但特別能表現(xiàn)他的民族意識(shí)和文化立場(chǎng)的是他的刪節(jié)。實(shí)際上,古英語(yǔ)詩(shī)人改寫(xiě)《舊約》故事的一個(gè)重要方面也是對(duì)源本中一些不符合盎格魯-薩克遜受眾的文化習(xí)慣、不適合游吟詩(shī)人演唱的內(nèi)容進(jìn)行刪節(jié)。
當(dāng)然中世紀(jì)詩(shī)人對(duì)其“翻譯”的文本大多進(jìn)行刪節(jié),瓦斯本人也是如此,他刪除了杰弗里《不列顛君王史》里包括梅林那十分冗長(zhǎng)但卻極富不列頓文化色彩的一系列晦澀的政治預(yù)言等內(nèi)容以弱化作品的不列頓文化元素。拉亞蒙對(duì)瓦斯的刪節(jié)中最有意義的是,他刪去了也許是瓦斯對(duì)杰弗里原作最重要的改寫(xiě)和他最具特色的貢獻(xiàn)。瓦斯用盎格魯-諾曼王朝所代表和提倡的宮廷文化改寫(xiě)杰弗里的“史書(shū)”,在亞瑟王部分增加了許多關(guān)于騎士精神和宮廷愛(ài)情的內(nèi)容,描寫(xiě)女士們觀看騎士比武和表現(xiàn)豪華優(yōu)雅的宮廷活動(dòng)。瓦斯在很大程度上將亞瑟王和他的武士們塑造成浪漫傳奇里風(fēng)度翩翩、勇武而高雅的騎士,使他的詩(shī)作具有相當(dāng)突出的浪漫傳奇風(fēng)格和色彩。由于這些改寫(xiě)主要是依據(jù)亨利二世和艾琳諾所倡導(dǎo)的宮廷文化、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和王室活動(dòng),瓦斯的《布魯特傳奇》自然有利于和服務(wù)于盎格魯-諾曼王朝在不列顛的統(tǒng)治更為合法化和合理化的政治和文化意圖,所以盎格魯-諾曼王室對(duì)他的《布魯特傳奇》十分贊賞。然而,拉亞蒙將瓦斯詩(shī)作中這些具有浪漫傳奇色彩和表現(xiàn)盎格魯-諾曼王朝宮廷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部分幾乎全部刪除,正如他將瓦斯原作標(biāo)題中的“傳奇”(roman,即“浪漫傳奇”)斷然刪去一樣。他刪去瓦斯作品中那些非常優(yōu)美、在當(dāng)時(shí)十分流行的具有突出浪漫傳奇色彩的部分,顯然是基于其文化立場(chǎng)而非為增加作品可讀性。他出于英格蘭人的身份認(rèn)同和對(duì)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抵觸情緒,似乎不愿接受瓦斯這些宣揚(yáng)盎格魯-諾曼王朝的宮廷文化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內(nèi)容,加之浪漫傳奇的風(fēng)格和特色也與他在敘述亞瑟王的英雄業(yè)績(jī)時(shí)使用的古英語(yǔ)史詩(shī)體裁和風(fēng)格不太兼容,所以他系統(tǒng)地將這些內(nèi)容刪除。另外,十分值得注意而且的確很有意義的是,后來(lái)在 14 世紀(jì)末出現(xiàn)的那部也使用頭韻體而且在那時(shí)期所有亞瑟王文學(xué)作品中最突出表現(xiàn)英格蘭民族意識(shí)的優(yōu)秀詩(shī)作《亞瑟王之死》,也幾乎沒(méi)有宮廷文化和浪漫傳奇元素,卻同拉亞蒙的《布魯特》一樣具有史詩(shī)性質(zhì)。
其實(shí),拉亞蒙刪除瓦斯源本里亞瑟王部分表現(xiàn)騎士精神和宮廷愛(ài)情的宮廷文化內(nèi)容,似乎也并不僅僅或者說(shuō)并不完全是源自他個(gè)人的好惡,因?yàn)樗?shī)作中宮廷文化的缺席,不僅在當(dāng)時(shí)甚至在隨后一個(gè)半世紀(jì)的中古英語(yǔ)文學(xué)中也并非孤例。拉亞蒙刪除來(lái)自大陸傳統(tǒng)的宮廷文化有更深層的原因,它反映出諾曼征服之后英格蘭社會(huì)和文化分裂的現(xiàn)實(shí)以及英格蘭本土文化的重大影響。在 12 世紀(jì)中期以后,當(dāng)宮廷文化在歐陸興起和以騎士精神和宮廷愛(ài)情為主題的浪漫傳奇文學(xué)在大陸流行和繁榮之時(shí),宮廷文化作為安茹帝國(guó)的主流文化也突出表現(xiàn)在英國(guó)文學(xué)中,但其影響主要限于盎格魯諾曼語(yǔ)文學(xué)。實(shí)際上,在 14 世紀(jì)中期喬叟創(chuàng)作出《公爵夫人書(shū)》之前,英語(yǔ)文學(xué)中沒(méi)有一首真正意義上的宮廷詩(shī)歌(Richmond 147)。
前期中古英語(yǔ)文學(xué)與宮廷文化的脫節(jié),一方面是因?yàn)槟菚r(shí)英語(yǔ)文學(xué)中原本就沒(méi)有表現(xiàn)宮廷文化的傳統(tǒng)。其次,植根于英格蘭普通民眾和英格蘭本土文化的英語(yǔ)文學(xué)與盎格魯-諾曼統(tǒng)治階級(jí)及其文化之間存在相當(dāng)距離,英語(yǔ)詩(shī)人們對(duì)還沒(méi)有英格蘭化甚至刻意不認(rèn)同乃至鄙視他們所統(tǒng)治國(guó)度的本土文化的統(tǒng)治階級(jí)頗為反感,所以他們對(duì)宮廷文化這種“異質(zhì)”文化敬而遠(yuǎn)之實(shí)際上也是一種政治姿態(tài)和文化策略。直到英格蘭王室和上層貴族在英法百年戰(zhàn)爭(zhēng)期間最終英格蘭化以及他們的宮廷文化最終同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統(tǒng)一的英格蘭民族文化,這種狀況才徹底改變;其重要標(biāo)志是,在英語(yǔ)文學(xué)大繁榮的喬叟時(shí)代,在不僅以喬叟為代表的倫敦派宮廷詩(shī)人們的作品里,而且在古英詩(shī)傳統(tǒng)的頭韻體詩(shī)歌復(fù)興運(yùn)動(dòng)的許多杰出詩(shī)作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中,都同時(shí)表現(xiàn)出宮廷文化和英格蘭本土文化以及它們的和諧與統(tǒng)一。
如果說(shuō)拉亞蒙刪除與盎格魯-諾曼王室相關(guān)聯(lián)的宮廷文化反映他對(duì)古英詩(shī)傳統(tǒng)的繼承和對(duì)英格蘭人文化身份的表達(dá)的話,那么他在改寫(xiě)瓦斯詩(shī)作時(shí)所給予的一些重要增添也是如此。在這方面,他對(duì)亞瑟王出生的描寫(xiě)很有意義。其實(shí)杰弗里、瓦斯和拉亞蒙對(duì)亞瑟王的出生的描寫(xiě)都很好地反映出他們各自的民族文化立場(chǎng)。在這一事件的敘述中特別有意義的是,亞瑟出生后,杰弗里將他交給不列頓傳統(tǒng)的代表魔法師梅林撫養(yǎng)以強(qiáng)調(diào)這位將征服歐洲的英雄的不列頓文化血統(tǒng)。瓦斯卻刪去了這一內(nèi)容來(lái)淡化亞瑟身上的不列頓色彩,這與他把亞瑟王盎格魯-諾曼化的整體傾向一致。最有意思的是拉亞蒙,他按《圣經(jīng)》里耶穌出生時(shí)東方三賢前來(lái)獻(xiàn)禮的情節(jié),描寫(xiě)仙女們前來(lái)向初生的亞瑟獻(xiàn)禮,只不過(guò)她們獻(xiàn)的不是東方三賢的黃金、乳香和沒(méi)藥,她們的禮物是使他“興旺發(fā)達(dá)”的“力量”“財(cái)富”和“長(zhǎng)壽”(Layamon 177-78)。更重要的是,拉亞蒙將初生的亞瑟交給擁有盎格魯-薩克遜“血統(tǒng)”的仙女們撫養(yǎng)。
拉亞蒙的改寫(xiě)增加了亞瑟王這個(gè)人物的神秘性,為他超凡的力量和輝煌的業(yè)績(jī)做了鋪墊。在這點(diǎn)上,拉亞蒙更接近杰弗里,他們都讓亞瑟由本土民間傳說(shuō)中具有神秘力量的梅林或仙女們撫養(yǎng)長(zhǎng)大以凸顯他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不同的是,拉亞蒙在這里把對(duì)亞瑟王朝的創(chuàng)建與興盛起到至關(guān)重要作用的那位不列頓魔法師改成仙女們,而他筆下的仙女 alven 是一個(gè)古日耳曼詞,也就是說(shuō),這些仙女是出自日耳曼傳說(shuō),因此代表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tǒng)。這樣,拉亞蒙就巧妙地把杰弗里筆下的不列頓英雄置于日耳曼文化傳統(tǒng)之中,這顯然與他致力于英格蘭化亞瑟王的基本傾向一致。實(shí)際上,仙女們賦予亞瑟王的力量、財(cái)富、長(zhǎng)壽(包括永恒聲名)以及隨即提到的慷慨等“禮物”正是日耳曼傳統(tǒng)的核心價(jià)值觀念。阿隆斯坦認(rèn)為,它們使亞瑟成為“一位貝奧武甫和赫羅斯加 a 類(lèi)型的盎格魯-薩克遜武士國(guó)王”(38)。正是依靠這些“禮物”,亞瑟王后來(lái)征服了“世界”;或如拉亞蒙所說(shuō):“這位國(guó)王將他的人民聯(lián)合在一起,生活在幸福之中;他靠這些東西,靠他兇猛之威力和不盡之財(cái)富擊潰了所有帝王”(Layamon 184)。任何讀過(guò)《貝奧武甫》的人都會(huì)注意到,該史詩(shī)用了大量篇幅強(qiáng)調(diào)英雄時(shí)代那些杰出的日耳曼國(guó)王們正是依靠“兇猛之威力”和慷慨的賞賜征服對(duì)手和獲得人們擁護(hù)。慷慨賞賜與力量密不可分,也是日耳曼文化中的核心價(jià)值。
可以說(shuō),拉亞蒙一直試圖將亞瑟王塑造成一位強(qiáng)悍的盎格魯-薩克遜武士君主,而非宮廷浪漫傳奇里那種溫文爾雅的騎士國(guó)王。他對(duì)瓦斯詩(shī)作特別重要的改寫(xiě)同時(shí)也特別能揭示亞瑟王身上強(qiáng)悍的盎格魯-薩克遜特質(zhì)的是關(guān)于圓桌出現(xiàn)的那部分。將圓桌引進(jìn)亞瑟王傳奇本是瓦斯的一個(gè)突出貢獻(xiàn);自那以后,圓桌成為亞瑟王朝的象征,烏托邦式的圓桌騎士團(tuán)體也成為中世紀(jì)騎士精神的最高體現(xiàn)。拉亞蒙在詩(shī)作中自然也保留了圓桌出現(xiàn)的內(nèi)容,但做了重大改寫(xiě)。在瓦斯書(shū)中,為防止騎士們因座次產(chǎn)生沖突,亞瑟王命人制作圓桌,于是騎士們的座位不分尊卑,大家平等相處,表現(xiàn)出宮廷的典雅與祥和,同時(shí)也反映出亞瑟王的睿智和對(duì)騎士們的愛(ài)護(hù)。整個(gè)過(guò)程的敘述不到半頁(yè),然而拉亞蒙卻為圓桌的出現(xiàn)增添了血腥沖突和亞瑟王嚴(yán)厲鎮(zhèn)壓的敘事,篇幅也長(zhǎng)達(dá)數(shù)頁(yè)。事件發(fā)生在圣誕慶宴上,參加者按地位尊卑在亞瑟王和王后以下落座,然而這些桀驁不馴的武夫很快就因?yàn)樽伟l(fā)生沖突,先是面包開(kāi)始飛,然后相互扔酒杯,隨即刀劍相向,于是一場(chǎng)混戰(zhàn),血肉橫飛,不少人死于非命。
亞瑟王對(duì)武士們竟然如此蔑視其權(quán)威深感震怒。他命令道:“全都坐下,而且要快,否則處死!”然后他下令將最先動(dòng)手之人用繩子拖到沼澤地淹死,并把他所有“近親的腦袋”用“寬刀”砍掉。他家族中女人也難逃厄運(yùn),她們的鼻子全被割去“以毀壞她們的容顏”,這樣她們就再也嫁不出去。亞瑟王說(shuō):“我要滅掉他的整個(gè)家族。”他宣布,如果再發(fā)生這樣的事,不論地位高低一律處死,并命令所有的人立即發(fā)誓遵守。在用血腥的手段結(jié)束這場(chǎng)混亂之后,他吩咐宴會(huì)繼續(xù),眾人懷著對(duì)“亞瑟王的恐懼”重新落座。后來(lái),一位自稱(chēng)手藝高超的智者建議為亞瑟王制作一張圓桌。他告訴亞瑟,有了圓桌,“直到世界末日,也不會(huì)再有情緒沖動(dòng)的騎士在你的宴會(huì)上打斗。”圓桌建成后,騎士們坐下吃肉喝酒,像“兄弟”和“戰(zhàn)友”一樣親密無(wú)間(209-12);圓桌上自然再也沒(méi)有爭(zhēng)端和打斗。
從瓦斯和拉亞蒙對(duì)圓桌出現(xiàn)這個(gè)亞瑟王傳說(shuō)中的核心事件大為不同的描寫(xiě)可以看出,他們代表不同的傳統(tǒng),而圓桌也體現(xiàn)不同的價(jià)值觀。瓦斯強(qiáng)調(diào)圓桌體現(xiàn)騎士精神,表現(xiàn)騎士們的平等和友誼,它維護(hù)著宮廷里的安定與祥和,是宮廷文化的象征,而下令建造圓桌的亞瑟王本人則是代表宮廷文化的騎士君王。然而在拉亞蒙詩(shī)作里,圓桌是由一位智者根據(jù)動(dòng)蕩沖突的現(xiàn)實(shí)和王權(quán)與秩序的需要提議建造,而它表面上代表的平等精神早已提前被發(fā)生在血腥沖突之后的殘酷鎮(zhèn)壓以及在死亡威脅下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亞瑟王面前發(fā)誓的情景所顛覆。所以這張圓桌真正體現(xiàn)的不是平等精神,而是亞瑟王的威嚴(yán),是至高無(wú)上的王權(quán)和騎士們被迫遵守的秩序。亞瑟王也不是溫文爾雅的騎士精神的代表,而是封建等級(jí)社會(huì)中掌握生殺予奪大權(quán)的專(zhuān)制君主和在任何時(shí)候都可能出現(xiàn)內(nèi)外沖突的血雨腥風(fēng)的中世紀(jì)英格蘭不可或缺的秩序維護(hù)者。相對(duì)而言,瓦斯詩(shī)作中的圓桌是富含理想色彩的浪漫意象,而拉亞蒙筆下的圓桌則是更具現(xiàn)實(shí)意義的王權(quán)象征。
由此還可以看出,除圓桌本身的象征意義外,這段關(guān)于圓桌出現(xiàn)的描寫(xiě)對(duì)亞瑟王的性格展示特別重要。拉亞蒙以此塑造出一位猶如在古英語(yǔ)英雄史詩(shī)里那類(lèi)在亂世中用鐵血手段維持權(quán)威與秩序的強(qiáng)悍君主。同樣展示亞瑟王威嚴(yán)形象的內(nèi)容和細(xì)節(jié)在拉亞蒙的改寫(xiě)中還有許多,比如在亞瑟王即將率大軍渡過(guò)海峽與羅馬決戰(zhàn)之時(shí),詩(shī)人增加了亞瑟王關(guān)于火龍與怪獸搏斗的噩夢(mèng)。亞瑟王驚醒后,“深感恐懼,大聲呻吟”,然而“在他自己說(shuō)出原因之前,天底下沒(méi)有騎士膽敢向他詢問(wèn)”。當(dāng)亞瑟王講出夢(mèng)境后,從“主教們”到“哲人們”以及圓桌騎士,全都競(jìng)相“盡其智慧”從“最好的方面解讀”,而“沒(méi)有人膽敢稍微朝壞的方向解釋?zhuān)驗(yàn)樗麄兌寂率?duì)他們很寶貴的肢體” (235-36)。這樣,詩(shī)人非常巧妙也很幽默地用屬下對(duì)他的敬畏來(lái)進(jìn)一步顛覆瓦斯詩(shī)作里騎士國(guó)王亞瑟那高雅仁慈的形象和他與圓桌騎士們那種親密無(wú)間的烏托邦關(guān)系。拉亞蒙如此對(duì)亞瑟王去浪漫化一直持續(xù)到他的亞瑟王朝戲劇的終場(chǎng)。
瓦斯的確也突出描寫(xiě)了亞瑟王朝的強(qiáng)盛與亞瑟王的權(quán)威,但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亞瑟王宮中和諧高雅的宮廷氛圍,賦予亞瑟王騎士品質(zhì)與美德,這樣他就將亞瑟王朝和代表新型宮廷文化的盎格魯-諾曼王朝在文化傳統(tǒng)上連接起來(lái),亞瑟王朝也就成為以亨利二世為代表的盎格魯-諾曼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先祖。與之相對(duì),拉亞蒙則通過(guò)系統(tǒng)刪除瓦斯附加在亞瑟王傳說(shuō)中的宮廷文化元素和亞瑟王身上的浪漫傳奇色彩,將他置于英格蘭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語(yǔ)境中,突出其威嚴(yán)的君主形象,并在故事中增加大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元素,從而將亞瑟王和他的傳說(shuō)英格蘭化。換句話說(shuō),拉亞蒙通過(guò)他的改寫(xiě),最終將瓦斯筆下盎格魯-諾曼式國(guó)王和杰弗里書(shū)中的不列頓國(guó)王成功改造成盎格魯-薩克遜或者說(shuō)英格蘭君主。他為亞瑟王安排的結(jié)局也表達(dá)了這一意圖。
在亞瑟王傳說(shuō)中最引起爭(zhēng)議、最令不列頓人動(dòng)感情同時(shí)也最突出地被賦予政治和文化意義的是亞瑟王的結(jié)局。當(dāng)亞瑟王戰(zhàn)勝羅馬大軍殺死羅馬皇帝后,正準(zhǔn)備進(jìn)軍羅馬之時(shí),國(guó)內(nèi)傳來(lái)他的外甥、攝政王莫德雷德 a 篡權(quán)叛亂的消息,他只得回師平叛。經(jīng)過(guò)殘酷決戰(zhàn),亞瑟王殺死莫德雷德,自己也身負(fù)重傷。早在杰弗里等人的“歷史”記載出現(xiàn)之前,關(guān)于亞瑟王負(fù)傷后被仙女們接到不列頓人的樂(lè)土阿瓦隆島,在那里治好了傷,正等待機(jī)會(huì)回到不列顛拯救他苦難中的人民的傳說(shuō)一直在民間廣為流傳,而且不列頓人對(duì)此深信不疑。1113 年,一群來(lái)自不列塔尼的修士手下一位仆人在康沃爾因竟敢質(zhì)疑亞瑟王還活著的傳說(shuō)而挨揍,而且盡管是在神圣的教堂內(nèi),還是引發(fā)了一場(chǎng)騷亂。
由于不列頓人堅(jiān)信亞瑟王會(huì)回來(lái)拯救他們,影響到王國(guó)的安定,因此盎格魯-諾曼王朝采取措施破除亞瑟王還活著的神話。亨利二世曾通知格拉斯哥修道院說(shuō),一位不列頓預(yù)言家告訴他,亞瑟王安葬在該修道院,并授意修士們尋找亞瑟王陵墓。他宣布自己和王后將去拜謁亞瑟王陵,但他還未能成行就于 1189 年去世。兩年后格拉斯哥修道院宣稱(chēng),通過(guò)發(fā)掘已發(fā)現(xiàn)亞瑟王和王后的遺骸,并說(shuō)墓中有刻著亞瑟王和王后名字的十字架。1227 年,愛(ài)德華一世在征服威爾士后,面臨不列頓人新的叛亂,于是他和王后率王公大臣于 1228 年復(fù)活節(jié)前往格拉斯哥拜謁亞瑟王陵,并大張旗鼓地將所謂的亞瑟王和王后遺骸遷葬新建的豪華陵墓。a 那是一個(gè)十分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既向不列頓人表明盎格魯-諾曼王朝是亞瑟王的繼承者,也向他們證明亞瑟王的確早已死去以斷其念想。
由于亞瑟王和他的結(jié)局已被賦予了濃厚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利益,杰弗里等編年史家以及后來(lái)的亞瑟王文學(xué)的作家們,包括三部著名的英語(yǔ)《亞瑟王之死》的作者,都對(duì)亞瑟王的結(jié)局精心處理,以表達(dá)自己的立場(chǎng)和思想意識(shí)。作為不列頓人,杰弗里顯然希望亞瑟王還活著;但作為編年史學(xué)者,他不得不同民間傳說(shuō)保持距離。所以他似乎只是在陳述事實(shí),說(shuō)亞瑟王受了“致命傷”,被送去阿瓦隆。至于他死沒(méi)死,杰弗里則不明說(shuō)。不過(guò),后來(lái)在撰寫(xiě)《梅林傳》時(shí),他似乎感到不必太受編年史體裁束縛;所以他在該書(shū)里說(shuō),受傷的亞瑟王被梅林和先知塔里森送到凱爾特人心目中永遠(yuǎn)春光明媚的樂(lè)土(fairyland),受到島上九個(gè)仙女之首仙女摩根(Morgan la Fay)照看。摩根答應(yīng),她將治好亞瑟并照看他,直到他離開(kāi)阿瓦隆回去拯救不列顛。
與之相反,瓦斯作為盎格魯-諾曼人,如同盎格魯-諾曼王朝一樣,自然不相信也不希望亞瑟王還活著。但作為喜歡描寫(xiě)奇異事件的浪漫傳奇詩(shī)人,在表面上,他還是像杰弗里一樣也對(duì)亞瑟王的結(jié)局做了模棱兩可的處理,沒(méi)明說(shuō)他是否活著。但他說(shuō):編年史撰寫(xiě)人“安慰”人們說(shuō),“亞瑟自己也受到致命傷。他 [編年史撰寫(xiě)人] 將他送到阿瓦隆治療。他還在阿瓦隆,不列頓人還在等待著他的歸來(lái)”(Wace 113)。有意思的是,是編年史家(自然是指其源本的作者杰弗里)而非傳說(shuō)中的仙女們或者魔法師梅林把亞瑟王送到阿瓦隆,而那也只是為了“安慰”那些在苦難中還滿懷期待的不列頓人。這其實(shí)很巧妙地否定了民間傳說(shuō),也間接顛覆了杰弗里的意愿。換句話說(shuō),他是在暗示:杰弗里是在撒謊。
拉亞蒙的處理更有其特別之處。他讓身負(fù)重傷的亞瑟王自己宣稱(chēng),他將前往阿瓦隆,與那些“最美麗的仙女們”在一起,“女王阿甘特,最美麗的仙子,將治好我的傷”, “將來(lái)我會(huì)回到我的王國(guó),同不列頓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阿甘特即仙女摩根。拉亞蒙隨即說(shuō):“不列頓人仍然相信他還活著,在阿瓦隆同最美麗的仙女們?cè)谝黄?不列頓人至今仍然期盼著他會(huì)回來(lái)。這個(gè)世界上沒(méi)有人知道真相,沒(méi)有人能講出更多關(guān)于亞瑟王的情況。但從前有位圣哲名叫梅林;他說(shuō)——他的說(shuō)法真實(shí)可信:一位亞瑟王將會(huì)來(lái)幫助英格蘭人”(264)。拉亞蒙首先讓亞瑟王自己說(shuō)他會(huì)回來(lái),隨即講不列頓人相信他會(huì)回來(lái),然后由詩(shī)人自己或敘述者出面說(shuō)沒(méi)有人知道真相,這實(shí)際上一步步減弱了亞瑟王回歸的可信度。也就是說(shuō),除了亞瑟王自己的承諾和不列頓人的信念之外,亞瑟王還活著并將回來(lái)之說(shuō)沒(méi)有任何其他根據(jù)。在這一點(diǎn)上拉亞蒙同瓦斯倒是比較一致。但瓦斯質(zhì)疑不列頓人關(guān)于亞瑟王還活著的傳言是出自盎格魯-諾曼王朝長(zhǎng)治久安的政治目的。相反,拉亞蒙顛覆不列頓人的傳言則是出于盎格魯-薩克遜人或者說(shuō)英格蘭人的利益。所以他借不列頓人最信任的梅林之口說(shuō):“一位亞瑟王將會(huì)來(lái)幫助英格蘭人”,并強(qiáng)調(diào)“他的說(shuō)法真實(shí)可信”。這是意義特別深刻的改寫(xiě)。他巧妙地在亞瑟王之前加了一個(gè)不定冠詞,于是將“亞瑟王”換作“一位亞瑟王”(an Arthur),同時(shí)又把“將回來(lái)”(will come back)改為“將會(huì)來(lái)”(will come)。這其實(shí)是在暗示,那位亞瑟王已經(jīng)死去,但另外一位像亞瑟王那樣的英雄將會(huì)出現(xiàn),然而他不是來(lái)拯救不列頓人,而是“幫助英格蘭人”。正因?yàn)槿绱耍瓉喢刹旁谠?shī)作中一直在竭力將亞瑟王英格蘭化。后來(lái)都鐸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亨利七世(1485—1509 在位)幾乎是如法炮制。他重新闡釋亞瑟王傳說(shuō),把自己說(shuō)成亞瑟王后裔,試圖要人們相信“不是亞瑟王自己,而是其后裔亨利七世在需要之時(shí)(玫瑰戰(zhàn)爭(zhēng)中)已經(jīng)回到不列顛恢復(fù)秩序”(Lupack 340- 41)。為了加強(qiáng)說(shuō)服力,他還將長(zhǎng)子取名亞瑟。
從杰弗里的《不列顛君王史》到瓦斯的《布魯特傳奇》,再到拉亞蒙的《布魯特》的演化,我們可以從一個(gè)特殊的角度看到諾曼征服后,特別是處于歐洲轉(zhuǎn)型期的 12 世紀(jì)文藝復(fù)興之環(huán)境中,英格蘭錯(cuò)綜復(fù)雜的社會(huì)、政治和民族狀況以及各種不同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博弈。三位作家從各自的民族、政治和文化立場(chǎng)書(shū)寫(xiě)不列顛“歷史”;在不同程度上,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將不列顛歷史,特別是其中的亞瑟王部分,講述成他們自己族裔的歷史,或者說(shuō)為自己族裔的政治文化服務(wù)。意在講述“英格蘭人之高尚業(yè)績(jī)”的拉亞蒙在兩位先驅(qū)的基礎(chǔ)上充滿自信地用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tǒng)和古英語(yǔ)英雄史詩(shī)風(fēng)格改寫(xiě)瓦斯詩(shī)作,使亞瑟王部分成為古英詩(shī)傳統(tǒng)的英格蘭民族史詩(shī);或如皮爾索爾(Derek Pearsall)所說(shuō),拉亞蒙的《布魯特》“以巨大的民族自豪之活力與熱情擴(kuò)展亞瑟王部分,使許多人將其宣布為第一部甚至是唯一一部英格蘭民族史詩(shī)”(16)。
但另一方面,這三部書(shū)寫(xiě)同一“歷史”的著作代表三個(gè)文化傳統(tǒng),這也反映出英國(guó)特別豐富多彩的歷史和文化,它們都是英國(guó)文化的核心組成。本文重點(diǎn)分析了拉亞蒙對(duì)瓦斯著作的改寫(xiě)和與杰弗里著作的互文,其實(shí)他選擇對(duì)他們的著作直接或間接進(jìn)行翻譯和改寫(xiě)本身就表明,他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對(duì)它們認(rèn)同。三位作者的立場(chǎng)、視角、利益和意圖不同,有時(shí)甚至對(duì)立,但在總體上,三部著作的基本內(nèi)容相同,而且三位作家對(duì)不列顛的歷史,特別是對(duì)亞瑟王朝的基本態(tài)度比較一致,都把亞瑟王塑造成民族英雄,都對(duì)亞瑟王朝的輝煌業(yè)績(jī)由衷地感到自豪。因此,由特洛伊人布魯特開(kāi)創(chuàng)和以亞瑟王朝為中心的不列顛“歷史”也就成為他們共同的歷史記憶。正因?yàn)槿绱耍覀冊(cè)谶@三部著作中也看到那三大文化傳統(tǒng)之間不僅有矛盾沖突,也有相互借鑒、影響與融合。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和三大族裔之間互動(dòng)日益密切,三大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也不斷加強(qiáng)。拉亞蒙對(duì)瓦斯以及對(duì)杰弗里的改寫(xiě)與互文預(yù)示著,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tǒng)與不列頓和盎格魯-諾曼傳統(tǒng)通過(guò)長(zhǎng)期的競(jìng)爭(zhēng)與融合,最終將在以盎格魯-薩克遜人為主體的統(tǒng)一的英格蘭民族在英法百年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形成之時(shí),共同建構(gòu)成以盎格魯薩克遜傳統(tǒng)為基礎(chǔ)的統(tǒng)一的英格蘭民族文化。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