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維特根斯坦在自己前后期的哲學思想中,從不同角度討論了認知、邏輯和言行的“正確”問題。不過,他非但沒有界定和辨析三種“正確”的不同含意,反倒經常將它們混為一談,結果造成了某些理論上的混亂。其實,辨析三者之間在語義方面的微妙異同以及互動關聯的關鍵,在于找到它們試圖“符合”的不同標準:認知正確在于符合事實,邏輯正確在于符合法則,言行正確在于符合規范。
關鍵詞 維特根斯坦;真;假;真理;認知;邏輯;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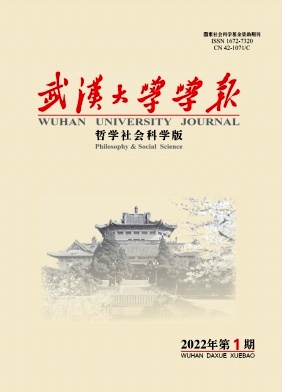
劉清平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01-05
維特根斯坦經常運用“richtig oder unrichtig”的概念(英譯者和中譯者一般分別譯為“right or wrong” “正確或錯誤”),并在不同語境下賦予它們不同的含義。這原本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問題在于,身為語言哲學大師,他非但沒有對這些含義做出嚴謹細密的界定辨析,反倒在許多情況下把它們混同起來,結果在某些重要問題上造成了對西方學界來說頗有代表性的理論扭曲。本文試圖圍繞《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的文本①,對這個問題做一些批判性的語義分析,澄清他在運用“正確”概念方面的模糊混亂,指出他因此陷入的悖論。
一、“正確”的語義內涵
一般來說,無論德語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還是英語的“right or wrong”,或是漢語的“正確或錯誤(不正確)”,主要包含了“對或錯”“正當或不正當”“合適或不合適”“恰當或不恰當”“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等相通的意思或語義,所以人們才能據此對它們互譯。有趣的是,《邏輯哲學論》也談道:“如果我知道了一個英文詞和一個同義德文詞的意思,我不可能不知道它們是同義的,也不可能不把它們互譯。”[1](4.243)反之,假如這兩個詞在核心語義上有很大區別甚至全不相干,把它們互譯就會偏離原文,造成誤導和扭曲。從這段論述看,維特根斯坦其實也承認,清晰地界定概念術語的核心語義,是我們準確地運用和譯讀它們,防止誤用和誤譯的前提。
進一步看,由于剛才提到的那些語義都浸潤著價值評判的意蘊,人們在日常言談里往往用這對概念指認各種東西對自己具有的或正面或負面的意義效應,如“你見義勇為是對的”“我接受不了榴蓮的味道”“割麥子的季節下雨真不合適”等。就此而言,它們顯然構成了人生在世展開價值評判的一對基本標準。此外,考慮到“richtig”以及“right”在詞源學上都與“右手(Rechte)”和“右邊(recht)”直接相關,我們還有理由猜測:最初大概是因為多數人習慣于用力氣更大更靈活的右手做事的緣故,說德語以及英語的人們才傾向于用這兩個術語評判各種行為的對、正當、合適、恰當、可以接受。事實上,在這兩種語言里,它們以及某些有著相似詞源的術語,還同時包含了“權益(權利)”“合法”“正義(公正)”“正直”“證成(辯護)”等道德意味濃郁的價值內涵[5]。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哲學論》也未加解釋地談到了命題的“平等權益或地位(gleichberechtigte,with equal rights or of equal rank)”[1](4.061,6.127),盡管語焉不詳,卻也從一個角度折射出維特根斯坦對“正確或錯誤”這對概念的非認知價值意蘊的自覺指認。
在現代西方哲學中,“richtig”與“gut”(“right”與“good”)的關系是一個爭議良久卻又莫衷一是的話題。由于主要涉及道德政治領域,漢語學界通常不是將這種關系譯成“正確”與“好”的關系,而是譯成 “正當”與“善”的關系。至于造成這種眾說紛紜的理論原因,首先是西方學界未能突破事實與價值的二元對立架構,找到“需要”這個能將兩者聯結起來的樞紐;其次是西方學界忽視了“諸善沖突”的要害,難以解釋何以在“善”之外還需要“應當”的內在機制[6]。鑒于這種關系對我們理解正確概念在不同語境里的不同含義十分重要,這里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筆者從元價值學視角提出的一種新解釋。
首先,由于善與需要的滿足直接相關,它在邏輯和時間上都先于正當:任何事實(客觀或主觀存在的東西、對象、事物、事情、事件等)如果有益于人們滿足需要,就會被人們評判為“善”的,覺得它們“可欲” 或“值得意欲”,得到了會愉悅快樂;反之,任何事實如果有害于人們滿足需要,則會被人們評判為“惡” 的,覺得它們“可惡”或“討厭反感”,遭遇了會痛苦難受。換句話說,善惡好壞是人生在世展開價值評判的第一對基本標準。
其次,正當與善之間存在等價的一面。因為對人們來說,有益而可欲的好東西自然也是合適恰當、可以接受的,有害而討厭的壞東西自然也是不合適不恰當、不可接受的。后果論主要就是依據兩者之間的等價一面,主張能夠產生善好后果的行為都是正當的,卻忽視了兩者之間還有不等價的一面。
最后,人們之所以會在“善惡好壞”之外另立“是非對錯”的評判基準,原因在于諸善沖突造成的兩者之間的不等價一面:在若干善相互抵觸、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在它們之間做出選擇,舍棄不重要的善而選取更重要的善,從而形成善惡交織的悖論性結構。這種悖論性結構集中表現在,對人們來說,一方面,更重要的善不僅本身是值得意欲的,而且在悖論性交織中也是合適恰當、可以接受的,所以應當選取;另一方面,不重要的善本身雖然值得意欲,卻會在悖論性交織中導致人們遭遇不可接受的嚴重損害,結果變成了不合適不恰當、不可接受的,所以應當舍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人們才不得不在善之外另行訴諸正當的標準,評判各種“值得意欲”的東西是不是在沖突中也是“可以接受”的。西方義務論(道義論)主要就是依據兩者之間的不等價一面,主張人們應當履行正當的義務,而無論產生怎樣的后果,卻忽視了兩者之間還有等價的一面:人們履行正當義務的目的,恰恰是為了確保更重要的善,防止不可接受的惡。
一個簡單的日常案例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上面的抽象分析:美味佳肴自然是可欲之善,因而人們一般也會認為它是合適恰當的。但倘若造成了過度肥胖,人們又把身體健康當成了更重要的好東西,他們會在沖突中認為:美味佳肴雖然“好”,但“不對”;反之,即便不喜歡粗茶淡飯,人們也會為了確保身體健康的重要目的而接受它,甚至不惜付出失去美味佳肴的代價。換言之,一旦各種好東西出現了沖突,就會造成某種悖論現象:“好”的不一定都“對”,反倒可能是“錯”的;“壞”的也不一定都“錯”,反倒可能是 “對”的。下面會看到,只有依據這種分析,我們才能說明維特根斯坦為什么會在不同語境里賦予“正確與錯誤”這對術語不同的含義,而他將這些含義混為一談又導致了怎樣的理論扭曲。
二、符合事實的認知正確
《邏輯哲學論》首先是在討論“非邏輯命題”通過描述事實構成了“真”的“圖像”的語境里運用正確概念的:“圖像必須與現實具有共同的東西,這樣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正確或錯誤地(richtig oder falsch,rightly or falsely)——展現現實”[1 (] 2.17);“圖像符合或不符合現實;它是正確或錯誤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right or wrong)、真或假的(wahr oder falsch,true or false)”[1](2.21)。同時,維特根斯坦緊接著就這樣解釋了“真”和“假”的概念:“要知道圖像是真還是假,我們必須拿它與現實比較。單從圖像本身不能知道它是真還是假。”[1](2.223-2.224)無需細說,這種主張“真和假”取決于認知是不是符合事實的見解,屬于真理問題上的“符合論”陣營,因而與主張“真和假”取決于認知是不是邏輯自洽的“融貫論”和主張“真和假”取決于認知能不能指導行為成功的“實用論”形成了鮮明對照。
盡管準確地指出了真理之為真理的本質所在,維特根斯坦在此把“正確或錯誤”的評判標準直接當成了“真或假”的同義詞,一并用來解釋“圖像符合或不符合事實”的特征,卻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兩對概念是分別位于價值維度和事實維度的深刻區別。更有甚者,這種等同還會在他的前期哲學里造成嚴重的自相矛盾,因為《邏輯哲學論》接下來曾依據事實與價值的二元對立架構主張:“如果存在某種有價值的價值,它必定位于一切發生和是其所是的東西之外”,無法像事實那樣通過命題表述出來[1](6.41-6.421)。按照這個見解,在涉及事實的“真或假”與涉及價值的“正確或錯誤”之間,必定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以至我們沒有理由將它們視為同義詞。
消除這個自相矛盾的唯一途徑,就是訴諸需要聯結事實與價值的樞紐效應:人們是在“求知欲”這種特定認知需要的推動下,從事描述事實的認知行為,取得要么符合真相、要么扭曲真相的認知成果的。所以,由于真理能夠滿足好奇心,人們就會覺得它們具有善的價值;由于謬誤不能滿足求知欲,人們就會覺得它們具有惡的價值。換言之,一旦將描述事實的認知成果與認知需要聯結起來,它們就會對人具有價值意蘊,以致“真”和“假”也有價值評判的語義內涵。所以,無論說的是哪一種語言,人們在日常生活里都會把真、善、美相提并論,視為人生在世的三大正面價值。維特根斯坦雖然在自覺論述中將事實與價值割裂開了,但他不僅借用了弗雷格的“真值(Wahrheitswert,truth-value)”概念[1](4.063)[7](P59),而且還在“序”里指出:“此書把思想表述出來了,并且表述得越好,價值就越大。……這里闡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來是無可辯駁和明確的。”[1](P20-21)結果,盡管與他主張價值位于世界之外的見解相抵觸,他在此卻明確肯定了“真”具有位于世界之內、并且能用“好”和“大”來評判的正面價值。
澄清了認知的“真假”特征通過認知需要的中介作用具有“善惡”價值的內在機制后,現在我們就能解釋為什么論題2.21幾乎是下意識地把“正確或錯誤”的價值術語與“真或假”的描述概念直接等同起來了:撇開與非認知需要出現沖突的情況不談,單就善與正當的等價一面看,在認知維度上,既然“真”是 “值得意欲”之“好”,它自然也是“可以接受”之“對(正確)”;既然“假”是“討厭反感”之“壞”,它自然也是 “不可接受”之“錯(不正確)”,所謂“真”的就是“對”的,“假”的就是“錯”的。換言之,維特根斯坦以及英譯者在此其實是基于善與正當在認知維度上的等價關系,才將“richtig”以及“right”直接當成了“wahr”以及“true”的同義詞來運用,將“unrichtig”以及“wrong”直接當成了“falsch”以及“false”的同義詞來運用,等于承認了:任何符合事實的“真”知識,都是合適恰當、可以接受的“正確”知識。
進一步看,維特根斯坦以及英譯者在論題 2.17 里不是將“richtig”以及“rightly”與“unrichtig”以及 “wrongly”對立起來,而是將它們與意指認知之“假”的“falsch”以及“falsely”不對稱地對立起來,也能得到解釋了:他們是基于“unrichtig”以及“wrongly”與“falsch”以及“falsely”屬于同義詞的理由,直接完成這種術語置換的。不用細說,中譯者也是基于類似的理由才不加辨析地把“richtig oder falsch,rightly or falsely”譯成了更通順的“正確或錯誤”,卻沒有死板地按照字面意思把它們譯成聽起來很別扭的“正確或假”①。
反過來看,下面的現象也容易理解了:德語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英語的“right or wrong”以及漢 語的“正確或錯誤”這些價值概念,除了包含第一節提到的那些適用于非認知領域的重合語義(“對和錯” “正當或不正當”“合適或不合適”“恰當或不恰當”“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外,往往還包含著“真實(真正)或虛假”“準確或不準確”“名實相符或名實不符”等適用于認知領域的重合語義。更有甚者,德語的 “korrekt oder unkorrect”(維特根斯坦較少用這對術語)以及英語的“correct or incorrect”(英譯者常用這對術語譯讀德語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可以說首先就有這種意指“真知”既好又對、“假知”既壞又錯的重合語義。盡管“政治正確”這個當前流行的術語將它們擴展到了非認知領域,讓它們在更廣泛范圍內構成了“richtig oder unrichtig”以及“right or wrong”的同義詞,這種語義層次上先后主次的微妙差異依然隱約可見,在漢語里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認知維度上,我們通常只說某種認知是“正確或錯誤”的,很少說它“正當或不正當”。
有鑒于此,盡管維特根斯坦的個別用詞有點亂,也沒有做出具體的說明,他在討論非邏輯命題之 “真”的語境里直接賦予“正確”一詞“符合事實”的意思,還是大體維系了兩個概念在限定范圍內的語義一致。誠然,由于語言長期演變的緣故,無論在日常言談還是學術話語里,任何字詞或概念都不會只有單一性的意思,而是往往像“正確或錯誤”那樣,通過種種語義關聯形成相互交織的多重性內涵,因此,在未加界定或澄清的情況下,很容易生成模糊不清、扭曲誤解的后果。不過,只要我們遵守邏輯同一律,在限定語境里讓每個字詞或概念保持同一種核心語義,一旦改變必須加以解釋并提供理由,我們還是能讓口頭言說或命題表述具有維特根斯坦很看重的“清楚明晰”的特征,避免發生混淆偷換這類邏輯上不對、不準確、不合適、不恰當、不可接受的現象。從某種意思上說,維特根斯坦以及某些哲學家嘗試運用或建立的“符號語言”“理想語言”“人工語言”,就是一些能夠嚴格貫徹同一律,讓每個字詞都以一個蘿卜一個坑的方式具有同一種核心語義的“邏輯語言”[1](3.325)。盡管這種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失敗了,我們卻沒有理由因此放棄在日常言談尤其是學術話語中遵守同一律的努力,相反,還應當盡可能實現他以“對于不能言說的東西必須保持沉默”[1 (] 7)的不清晰方式提出的那條經典要求:雖然對我們“不能”言說的東西我們“沒有能力”言說,因而“只能”沉默,但對我們“能夠”言說的東西,我們(尤其學者)卻“必須”遵守邏輯法則,努力清晰地言說,不然還不如不說。
三、符合法則的邏輯正確
反諷的是,在闡發《邏輯哲學論》這條經典要求的過程中,維特根斯坦卻出現了一些混淆概念的邏輯失誤,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模糊混亂:在“與事實比較并符合事實”的核心語義上運用“真”以及“正確”概念指認了“非邏輯命題”的特征,宣布“沒有先天為真的圖像”[1](2.225)后不久,他未作解釋地就將這兩個概念移植到了他認為與事實無關的“邏輯命題”上,主張“一種先天正確(richtiger,true)的思想,是一種其可能性就決定了它的真(Wahrheit,truth)的思想”[1](3.04)。后來,在談到數學命題時,他也以類似的口吻指出:“數學命題能夠證明只是意味著:它們的正確性(Richtigkeit,correctness)無需把它們表述的東西與涉及正確性的事實加以比較就能看出。”[1](6.2321)于是生成了一道棘手的難題:無需與事實比較就能 “先天為真”或“先天正確”的命題,還能在符合事實的嚴格意思上稱為“真”或“正確”的嗎?
不僅如此。在指出“命題顯明了它言說的東西,重言式和自相矛盾則顯明了它們什么都沒說”[1](4.461)的區別后,維特根斯坦接著又比較了它們在“真”的程度方面的等級差異:“重言式的真是確定的,命題的真是可能的,自相矛盾的真是不可能的。”[1](4.464)至于他宣布“邏輯命題的特征在于人們僅僅從符號中就能知道它們是真的……非邏輯命題的真假屬性不能單憑命題本身來確認”[1](6.113),更是用二者的鮮明對照坐實了他有混淆概念的嫌疑:假如在是否需要與事實比較來確認其真假這一點上,兩類命題有著如此涇渭分明之別,我們怎么有理由同時運用本應在同一語境里維系同一語義的“真假”概念來形容它們,甚至比較它們的等級差異呢?遺憾的是,盡管漏洞如此明顯,當前某些邏輯學教材仍然未加批判地接受了這種將三類不同的“真”相提并論并加以比較的說法[9 (] P379-381)[10(] P40-420)。
誠然,人們的確經常說,某個描述了事實之“真”、在認知上“正確”的命題在邏輯上也是“正確(對)” 的。但問題在于,前后兩個“正確”概念的核心語義是不是同一的,以致可以說這個命題在邏輯上也是 “真”的呢?很不幸,按照維特根斯坦自己界定的“真”概念,答案是否定的:既然命題只有在符合事實的前提下才是“真”的,并且因此被評判成認知上“正確”的,那么,在“什么都沒說”、因而沒法與事實比較、失去了“符合事實”這個必要前提的情況下,即便某個命題在邏輯上是“正確”的,我們也沒有理由因此將它說成是“真”的,否則就違反了對于保持邏輯“正確”來說至關緊要的同一律,混淆甚至偷換了“真”概念的核心語義,尤其會在比較所謂“無條件真”“可能真”和“不可能真”的時候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這里比較的是同一個意思的“真”嗎?
更反諷的是,由于維特根斯坦自覺地主張邏輯命題“什么都沒說”,有時也不得不承認,邏輯正確與認知正確有所不同,其意義在于命題及其推理的形式結構由于“符合法則”所達成的“清楚明晰”:“如果兩個命題相矛盾,或者一個命題從另一個命題推出,它們的結構就顯明了。……只要我們的符號系統中一切都是合適的,我們就掌握了正確(richtigen,right)的邏輯概念”[1](4.1211-4.1213);“如果存在邏輯的原初記號,正確(richtige,correct)的邏輯必須澄清它們的相對地位,并且證成(rechtfertigen,justify)它們的存在。由原初記號構成的邏輯結構必須是清晰的”[1](5.45)。顯而易見,這里所謂的“清楚明晰”,主要體現在組成命題以及推理的字詞符號之間的必然性語義關聯(即他認為高于“因果必然性”的“邏輯必然性”)上:正像同義反復的重言式那樣,如果能從某些字詞符號的核心語義中以一定如此的必然方式推出另一些具有同一語義的字詞符號,我們單從這種語義關聯中就足以知道它們是邏輯上“正確”的了。維特根斯坦正是在這個意思上宣布:“邏輯總是可以這樣來理解:每個命題都是它自己的證明”[1](6.1265); “數學的每個命題必須是自明的”[1](6.2341)。至于他主張“邏輯哲學”旨在“澄清思想……使命題明晰” 的基本使命[1 (] 4.112),當然也只有嚴格遵守那些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法則(特別是同一律)才能實現了。
就此而言,為了彰顯邏輯正確與認知正確的區別,我們其實應當把前者稱為“明”而不是“真”,并從這個角度理解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我們好像是在‘預設’‘邏輯之真’。我們事實上能像預設某種適當的符號體系那樣預設它們。”[1](6.1223)畢竟,雖然我們不可能在“符合事實真相”的意思上“預設”非邏輯命題的“真”,我們卻能夠在“符合邏輯法則”的意思上“預設”邏輯命題之“明”。至于維特根斯坦的失足之處則在于,他沒有意識到邏輯正確與認知正確的這種差異,反倒以指鹿為馬的方式指“明”為“真”,把符合論意思上的“描述事實之真”偷換成融貫論意思上的“邏輯自洽之真”,從而在真理本質的問題上用融貫論否定了他最初認同的符合論[11](P38)也是由于這種違反同一律的邏輯失誤,他的邏輯哲學不僅扭曲了邏輯正確在于“符合法則之明”、不在“符合事實之真”的本來面目,而且生成了某些說不通的自相矛盾,以致可以說是認知和邏輯上都不正確。
進一步看,導致維特根斯坦出現上述失誤的一個重要誘因是,他沒能把邏輯要求的符合法則之正確與邏輯學追求的符合事實之正確區分開。一方面,邏輯是指思維和語言在語義關聯上遵循的種種必然法則,也就是他的前期哲學強調的思維和語言在同一中具有的共通結構;人們(包括研究邏輯學的學者)只有恪守這些邏輯法則,才能維系命題及其推理的各部分之間合適恰當、可以接受的語義關聯,在思維和言說中達成清楚明晰的正面價值(認知維度上的“理性”也是因此與“邏輯推理”融為一體的),確保它們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否則的話,任何背離邏輯法則的思維和語言,都會像他那些指“明”為“真”的論述一樣,由于違反同一律失去清楚明晰的價值,淪為邏輯上的不正確。另一方面,各種邏輯學理論(包括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在把邏輯法則當成“事實”來研究的時候,又應當像其他學科的理論研究自己的對象那樣,首先基于求知欲如其所是地描述它們的真相(如邏輯正確是什么意思,它與認知正確有著怎樣的區別和關聯,同一律的功能何在,等等),否則的話就會像維特根斯坦那些指“明”為“真”的論述一樣,由于扭曲了邏輯正確的本來面目失去真的價值,淪為認知上的不正確。事實上,他不僅承認人們繪制的“事實的圖像”即“命題”是“一種事實”[1](2.1,2.141),而且還把“邏輯命題的先天為真”和“非邏輯命題的真假屬性”說成是邏輯哲學中“最重要的事實”[1](6.113),并在這種語境里要求人們對邏輯命題做出認知上“正確(richtige,correct)的解釋”[1](6.112)。不難看出,這些論述已經潛藏著“邏輯學應當成為一門正確揭示邏輯法則、因此具有真值的科學分支”的含義了。
可是,部分是由于“Logik”一詞兼有“邏輯”和“邏輯學”兩層語義的緣故,另一部分也是由于未能辨析認知正確與邏輯正確微妙差異的緣故,維特根斯坦沒有自覺意識到邏輯學理論(包括他的邏輯哲學)理應具有的雙重使命:一方面應當如實揭示邏輯法則的本來面目,成為“符合事實之真”的認知正確,另一方面應當恪守邏輯法則的內在要求,通過清楚明晰地運用概念、表述命題,成為“符合法則之明”的邏輯正確,結果隨意將兩者混為一談,最終導致自己的邏輯哲學在處理兩種“正確”的關系問題時,由于既遮蔽事實、又混淆概念的雙重失誤,陷入了認知上不“真”、邏輯上不“明”的尷尬境地,甚至否認了邏輯學有資格成為一門能將“真值”命題“正確”地表述出來的“科學”分支。
四、認知正確與邏輯正確間的張力
在認知正確與邏輯正確的關系問題上,維特根斯坦的另一個嚴重失誤是,由于把邏輯必然性置于因果必然性之上,主張邏輯命題的“無條件真”高于非邏輯命題的“可能真”,他的邏輯哲學顛倒了兩種正確的主次地位,再次落入了認知和邏輯上都不正確的自敗泥潭。
由于邏輯正確直接涉及思維和語言,它像認知正確一樣主要位于認知尤其理性認知的層面。同時,從需要和價值的關系角度看,如果說符合事實的認知正確來自“求知欲”,符合法則的邏輯正確則可以說來自“求晰欲”。在兩者的互動中,由于認知的目的在于探索事實真相,求知欲明顯占據了主導地位,求晰欲則處于從屬地位,旨在讓真理知識具有清楚明晰的價值。畢竟,如果不涉及非認知需要,單從滿足認知需要的角度看,虛假的知識哪怕邏輯上再清晰,也是匱乏積極意義的。維特根斯坦將邏輯比做“腳手架”[1](4.023,6.124),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它的工具屬性;但奇怪的是,他在《邏輯哲學論》里又通過混淆兩種不同“正確”的途徑,讓邏輯正確以喧賓奪主的方式占據了根基的地位。
其實,維特根斯坦在指“明”為“真”后,又對邏輯命題的“無條件真”與非邏輯命題的“可真可不真”加以比較,已經流露出把偏重語義形式的邏輯正確凌駕于偏重事實內容的認知正確之上了,卻忘了自己強調過的那一點:各種事實是在“邏輯空間”中相互聯結的,因而命題也只能在“邏輯空間”中描述它們[1](1.13-2.202)。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任何命題都同時包含了描述事實的認知一面和關涉法則的邏輯一面,所以既不存在“與邏輯有關卻什么都沒說”的“邏輯命題”,也不存在“說了些什么卻無關于邏輯”的 “非邏輯命題”,否則的話,事實、思維和語言共同具有的“邏輯結構”也將不復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即便在重言式和自相矛盾中,由于組成它們的主要字詞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描述事實的核心語義,認知一面也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構成了這些字詞的語義關聯是否符合邏輯法則的先決前提。因此,我們根本不可能像維特根斯坦主張的那樣,無需訴諸字詞語義描述事實的實質性內容,抽象地評判它們的形式關聯在邏輯上是否正確,乃至預設某種適當的符號體系是否為“真”。例如,“單身漢是沒結婚的男士”之所以是個認知和邏輯上都正確的重言式,根本原因與其說是我們憑空預設了“漢”與“男士”具有同一語義的符號體系,不如說是這個符號體系在描述同一個事實的“漢”與“男士”兩個字詞之間建立了符合同一律的語義關聯。
從這里看,重言式的所謂“無條件真”就僅僅意味著,它的各部分之間的形式性語義關聯由于完全符合同一律的緣故,在邏輯上是無條件正確的,卻不等于說它也一定完全符合事實,在認知上同樣是無條件正確的。像“金山是金子堆成的山”的重言式,在邏輯上當然是無條件正確(對)的,但這既不意味著它在認知上“什么都沒說”(它明顯言說了金山這個東西),也不意味著它在描述自然事實方面也是認知上無條件正確(真)的。相反,盡管它的語義關聯的清晰程度如同一塊玲瓏剔透的水晶,但除了像維特根斯坦這類不接地氣的哲學家外,人們還是不會覺得它比“山上長滿了樹木”的“可真可不真”命題更有描述事實的正面價值,因為地球上本來就找不到一座由金子堆成的山。與此類似,盡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因此蘇格拉底有死”的推理建立在兩個認知正確的前提上,因此可以說是認知上的“無條件真”,但我們也不要忘了事情的另外一面:盡管“人皆不死,蘇格拉底是人,因此蘇格拉底不死”的推理也是邏輯上的“無條件正確(對)”,但恰恰由于大前提扭曲了事實的緣故,它根本就不是認知上的“無條件正確(真)”。有鑒于此,我們當然沒有理由顛倒認知正確與邏輯正確的主次關系,在指“明”為“真”后又反客為主地主張:邏輯命題的“無條件真”在正確程度上高于非邏輯命題的“可能真”。
對于自相矛盾的所謂“不可能真”也應當作如是解:由于將語義上彼此沖突的字詞語句關聯在一起,它在邏輯上明顯是不正確亦即“不可能明”的,讓人難以確定地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過,這既不意味著它在認知上“什么都沒說”,也不意味著它說的一定就是認知上的“不可能真”或“無條件假”。例如,“位移中的物體在某一刻既在又不在某一點上”就是一個邏輯上不正確的自相矛盾,沒能清晰地告訴人們這個物體在某一刻到底在不在某一點上,所以才被維特根斯坦說成是“邏輯上不可能”的[1](6.3751)。然而,恰恰由于它以不確定的方式如實描述了一個處于不確定狀態的物體位置,因此在符合事實之真的程度方面不僅高于“位移中的物體就在某一點上”或“不在某一點上”這類雖然清晰卻又片面的命題,而且也高于維特根斯坦舉出的“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這類雖然邏輯上“無條件對”、認知上卻匱乏確定性內容的重言式[1](4.461),甚至還會由于它的認知正確,讓它的邏輯不正確變得不那么嚴重了,以至人們不得不在認知上“接受”它包含的那種雖然自相矛盾、卻又認知正確的語義關聯。值得一提的是,當前邏輯學界從“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角度討論作為自相矛盾特殊形式的邏輯“悖論”[12](P1)[13](P32-47),似乎更切近“正確”特別是“邏輯正確”的內涵。所以,倘若能從這個角度進一步辨析認知正確與邏輯正確的微妙異同,或許有助于我們找到問題的謎底。
同樣富于反諷意味的是,維特根斯坦自己也曾未加論證地指出了兩種正確分別作為“真”和“明”的反差:“如果從‘一個命題對我們來說是明晰的’推不出‘它是真的’,明晰性就不足以證明它的真理性。”[1](5.1363)有鑒于此,他不惜付出混淆概念的代價,也要把“符合法則之明”的邏輯正確說成是高于“符合事實之真”的認知正確,或許只能歸因于他對邏輯哲學的特殊偏愛了。事實上,他在《邏輯哲學論》里一方面主張“一切真值命題的總和就是作為整體的自然科學”[1](4.11),斷言“哲學不是一種自然科學”[1](4.111),另一方面又強調“邏輯充滿了世界,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邏輯的界限”[1](5.61),因而只有邏輯哲學才能提供“唯一嚴格正確(richtige,correct)的方法”[1](6.53),幫助人們“正確地(richtig,rightly)看世界”[1](6.54),就流露出主張“無條件真”的邏輯哲學高于“可能真”的自然科學的扭曲意向。在20年后的《哲學研究》里反思“邏輯是以什么方式成為崇高的”問題時,他依然這樣概括了自己的前期見解:“邏輯似乎具有某種特殊的深度——某種普遍的意義。邏輯似乎位于所有科學的根基處。因為邏輯探究一切事物的本質。它努力尋找事物的根基,不關心事情實際上是怎樣發生的。”[2 (] §89)細究起來,這大概就是他在前期哲學中堅持指“明”為“真”的潛意識深層原因吧:如果說科學的本質在于“真”而不在于“明”,那他只有首先把兩種正確混為一談,將邏輯正確的“符合法則之明”也說成是“真”,才能進一步論證,“不關心事情實際上是怎樣發生的”、只是工具性地“澄清思想……使命題明晰”的邏輯,可以為作為“一切真值命題總和”的所有科學奠定“根基”。不然的話,一旦將他自己給出的“明晰性不足以證明真理性”的正確命題在邏輯上貫徹到底,他自己全力彰顯的邏輯作為“科學根基”的崇高地位就會轟然垮塌了。
糾正了維特根斯坦在認知和邏輯上的雙重謬誤后,我們就可以全面理解兩種“正確”的張力互動了:一方面,認知正確不僅與邏輯正確截然有別,而且在認知活動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出現沖突的時候甚至可以壓倒邏輯正確。所以,一個邏輯上不正確的自相矛盾如果揭示了事實真相,依然是認知上正確的,具有正面價值;反之,一個邏輯上正確的重言式如果扭曲了事實真相,依然是認知上不正確的,缺乏正面價值。另一方面,邏輯正確又是達成認知正確的有效工具,能夠發揮“澄清思想……使命題明晰”的積極功能,將正確認知以清楚明晰的方式表述出來,避免語言表述的模糊混亂遮蔽事實的本來面目。所以,一個描述事實存在的確定狀態的命題如果只是認知上正確而邏輯上不正確,就會包含不清楚不明晰的嚴重缺陷。就此而言,我們在認知活動中自然應當首先追求符合事實的認知正確,然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追求符合法則的邏輯正確,卻不可像維特根斯坦那樣,通過混淆概念把邏輯正確凌駕于認知正確之上,甚至顛倒主次地主張:不是認知正確為邏輯正確奠定了根基,而是邏輯正確為認知正確奠定了根基[14]。
五、符合規范的言行正確
除了認知維度上符合事實的認知正確和符合法則的邏輯正確外,維特根斯坦還討論了非認知維度上符合“規范”的言行正確,其內容涵蓋了道德、實利、信仰、炫美等價值領域。需要說明的是,他在談到第三種正確的時候,多數情況下用的是“規則(Regel,rule)”而非“規范(Norm,norm)”。本文采用非認知價值意蘊更為濃郁的“規范”一詞,主要是有助于我們辨析非認知維度上的言行正確與認知維度上的邏輯正確之間的微妙差異。這種差異在漢語里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如同第一節所說,人們往往會用“正當”一詞指稱言行正確特別是實踐行為的正確,卻很少用它指稱邏輯正確以及認知正確。
在《邏輯哲學論》里,維特根斯坦雖然主張倫理學不能用命題表述出來,卻又通過一些命題表述了他對倫理賞罰的看法:“確立‘你應當……’形式的倫理法則(Gesetze,law)的第一個思想是:‘如果不這樣做會怎樣呢?’……這個問題的提法中必定有某些東西是正確(richtig,right)的。必定有某種倫理上的賞罰,但它們必定包含在行為自身中。(同樣清楚的是,獎賞必定是可以接受(Angenehmes,acceptable)的東西,懲罰必定是不可接受(Unangenehmes,unacceptable)的東西。)”[1](6.422)按照“Angenehmes”和“Unan‐ genehmes”的原初語義,它們也能譯成“愉快(pleasant)”和“不愉快(unpleasant)”。但如果從善與正當的等價一面看,把它們譯成“可以接受(acceptable)”和“不可接受(unacceptable)”,似乎更能凸顯這個問題的“正當性(正確性)”意蘊,并且揭示一個簡單的道德事實:倘若某個行為符合了主導性的道德規范(廣泛認同的“你應當”),人們就會認為它是“正當”或“可以接受”的,甚至還會獎勵行為者,讓他感到“愉悅快樂”;反之,倘若某個行為違反了主導性的道德規范,人們則會認為它是“不正當”或“不可接受”的,甚至還會懲罰行為者,讓他感到“痛苦不快”。此外,在前期筆記里,維特根斯坦還站在某種規范性的立場上,斷言自殺作為“基本罪”是“不允許”亦即“不可接受”的,并認為這一點澄清了倫理的本質[8](P662- 663)。就此而言,與維特根斯坦主張的相反,倫理學的規范性部分不僅可以用包含非認知意蘊的命題表述出來(如“自殺是不可接受的”或“助人為樂是一種高尚的德性”),而且倫理學的科學部分也能像他在論題6.422中所做的那樣,用在元倫理學維度上揭示了賞罰本質的正確命題表述出來——雖然這個實然性論題仍然存在一些邏輯上的模糊之處,尤其沒有自覺地涉及善與正當的復雜關系。
在《哲學研究》里,維特根斯坦更頻繁地討論了符合規范的言行正確問題。這種轉向源于他對前期哲學的“嚴重謬誤”的自覺批判:偏重于探討思維和語言描述事實的認知性功能,尤其是專注于探討邏輯哲學使命題明晰的單一性功能,卻忽視了“語言游戲”在“生活形式”中通過與實踐行為的交織以“語意即語用”的方式發揮出來的多樣性效應[11](P59-61)。所以,他在后期哲學中更看重語言在命令、演戲、說笑、致謝、詛咒、祈禱等方面的訴求功能,主張“命令、提問、講故事、聊天就像吃喝行玩一樣,是我們自然史的一部分”[2](§23-27),從而完成了從關注語言與事實描述的認知性關聯到關注語言與價值訴求的非認知關聯的理論轉型。盡管維特根斯坦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也有些矯枉過正,相對貶低了認知正確和邏輯正確的重要意義,卻又圍繞語言與非認知行為的交織,針對如何實現符合規范的言行正確問題提出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見解。
維特根斯坦認為,“游戲是按照特定規則進行的。……它是游戲自身的工具……就像支配著玩游戲的自然規律(Naturgesetz,natural law)那樣。——但在這種情況下,旁觀者怎樣辨別游戲者玩得錯誤還是正確(richtigen,correct)呢?——游戲者的行為中存在著游戲的某些獨特標記”[2](§54)。換言之,人們要想“正確”地玩游戲,關鍵在于符合游戲的規范,如同人們按照路標行進那樣:“正確(richtige,right)的步驟就是與命令符合的步驟。”[2](§186)不過,大概出于與前期哲學劃清界線的考慮,維特根斯坦現在不再強調單一確定的邏輯正確了,也不再認為邏輯法則是先天預設、隱藏在現象背后的了,卻更傾向于主張人們是在日常實踐中約定俗成地形成了那些只是“家族相似”、缺乏共同本質的游戲規范特別是語言規范的,并認為人們可以通過后天的訓練和學習把握它們:“一條規則怎么能告訴我在這一點上必須怎樣做呢?……我曾受過訓練對路標做出特定的反應,于是我現在就對它做出這樣的反應了。”[2](§198)所以,“我們叫做‘命題’‘語言’的東西并沒有我想象的那種形式統一性,而是由或多或少相互關聯的諸多結構形成的一個家族。——但現在邏輯成了什么呢?它的嚴格性似乎在此消失了”[2 (] §108)。即便談到邏輯學是一門“規范性(normative,normative)科學”的時候,他也改變了以前強調邏輯必然性的嚴厲口吻,變得開放和寬容了:“我們不能說運用語言的人們必須玩這樣的游戲……仿佛要指明一個適當的語句是怎樣的,非得邏輯學家出面不可”[2 (] §81);相反,只要能在正常情況下完成任務,“只要不妨礙你看到事情是怎樣的,你說什么都隨你的便”[2](§79,87)。這種矯枉過正是如此激進,他甚至延續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把“邏輯空間”說成是“語法空間”的意向,把“邏輯正確”也籠統地說成是一種“語法正確”[8](P345-346)[11(] P80-81):“我們的研究是一種語法研究”,主要通過消除有關字詞用法的誤解,讓表述變得更確切以澄清問題[2](§90-91);“在字詞的用法中,我們可以把‘表層語法’與‘深層語法’區別開來”[2](§664)。
于是,與“語意即語用”的后期理念根本一致,維特根斯坦開始強調語言用法在日常言說和實踐行為中不那么理性嚴格、更富于感性趣味的“正確性”:“圖像就在那里,我不否認它的正確性(Richtigkeit,cor‐ rectness)。但它的應用是什么?”[2](§424)“我是怎么找到‘正確(richtige,right)’字詞的?我是怎么選擇字詞的?無疑有時我是按照它們氣味的微妙差異比較它們的:那個太……,那個也太……,這個才是對的。”[2](P334)談到“我把記號與感覺的聯結印在心中”的時候,他甚至宣布:“這個過程使我將來能夠正確地記起這種聯結。但在這個案例中我沒有評判正確性(Richtigkeit,correctness)的標準。人們會說,在我看來任何正確的東西都是正確的。而這只是意味著在此我們不能談論‘正確’。”[2](§258)這種相對主義的態度發展到極端,自然就是所謂的“怎樣都行”了:“隨便什么——因此也就等于沒有任何——東西都是正確的(Es stimmt alles—und nichts,Anything—and nothing—is right)。”[2 (] §77)
從這些論述看,由于訴諸“家族相似”的理念探討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一方面遠不像前期哲學那樣追求清楚明晰的邏輯正確,反倒時常處在說不清楚各種語言游戲有哪些相同和相異之處的模糊狀態,結果在相對主義傾向中流露出語焉不詳的弊端;另一方面,這些見解又從一個角度指出了言行正確的本質特征:由于位于非認知維度上,言行正確不像基于認知需要的認知正確和邏輯正確那樣,必須嚴格精確地符合事實和遵守法則,而主要取決于能不能按照相對寬松的應用規范(尤其是廣泛認同的“共識”或“習俗”),有效地滿足人們在“生活形式”中形成的非認知需要。所以,只要有助于達成非認知的目的,人們按照自己對語法、路標、棋譜這類規范的不準確解釋展開的言行活動,就依然是合適恰當、可以接受的,能夠稱為“正確”或“正當”。
有必要指出的是,維特根斯坦還談到人們對同一個字詞的不同理解和運用會不會出現沖突的問題: “我們瞬間把握的東西能不能與某種用法符合一致,適合不適合這種用法?……我們充其量不過是受到了某種心理上而非邏輯上的強制力。……只要圖像讓我們期望有不同的用法,就存在沖突的可能,因為人們一般是像這樣運用這個圖像的。我要說的是,這里存在正常和不正常的情況。只有在正常情況下才能清晰地確定詞語的用法。”[2](§139-142)的確,按照第一節的分析,我們只有訴諸“沖突”才能解釋語法規范中善與正當的不等價一面:在日常言談里,人們最初是隨心所欲地以不同的方式各說各話,甚至還會隨口說出像“牛奶我糖”這樣的語句[2 (] §498),結果造成了難以相互理解的局面。為了克服這類常見的沖突,人們才會約定俗成地確立公認的語法規范[維特根斯坦把它們叫作與“真假”有別、位于生活形式維度上的“共識”[2](§241-242)],主要憑借心理或語法上的強制力,約束人們的日常言談,確保人際交流的正常展開。否則的話,假如不存在沖突,再多樣化的言說方式都將是和諧無間、合適恰當的,既談不上正常和不正常的區別,也談不上按照盡管寬松了許多、卻仍然具有強制力的語法規范“應當或不應當” 怎樣言說的問題了。
從這個視角看,經常被后期維特根斯坦混為一談的“邏輯”與“語法”,其實還是存在某些很難用“家族相似”理念搪塞過去的微妙區別的:邏輯主要是在語言與思維的同一中,圍繞字詞語句描述事實存在的嚴格意思(認知性語義)展開,仿佛是以“先天預設”的方式確立那些普遍適用于所有語言、充滿理性強制力的共同法則,以確保理性思維的清楚明晰。語法主要是在語言與行為的統一中,圍繞字詞語句幫助人際交流的寬松運用(非認知語用)展開,通常是以“約定俗成”的方式確立那些分別適用于不同語言、強制力也比較弱的特定規范,以確保言說交談的清楚明晰。所以,一方面,不管在哪一種語言里,只要違反了邏輯同一律指“明”為“真”,都必然導致人們的言說出現不可接受的混亂結果;另一方面,人們不僅在不同的語言里可能遵守不同的語法規范[維特根斯坦就提到,“在俄語里人們不說‘石頭是紅的’而說‘石頭紅’”[2](§20)],而且哪怕是在同一種語言里,只要能夠完成正常的交流,人們也會以不同的方式言說[維特根斯坦就提到,人們在建筑工地上可以通過“遞給我一塊石板!”或“石板!”的不同呼喊,來表達同樣的訴求[2](§19)]。我們甚至能從這個視角進一步解釋“修辭”的特點:按照富于藝術感染力的恰當規范,表達人們的意愿、情感、想象和理念,以求產生更有吸引力的可欲效果。所以,與邏輯正確以及語法正確相比,修辭正確的標準通常更為寬松,強制力的程度也大為遜色。
值得一提的是,《哲學研究》在比較數學真理(Wahrheit,truth)與加冕禮的“錯誤走法”時,用了 “falsch”一詞,英譯者卻分別用了“wrong”和“false”兩個詞譯讀它[2](P346)。不過,要是我們在《邏輯哲學論》的嚴格意思上理解“falsch”或“false”的話,用它們評判加冕禮明顯不合適,因為如果說“二乘二等于五”的命題是因為不符合事實才“錯”了的話,當我們說加冕禮中某個步驟“錯”了的時候,并不是指它遮蔽了事實的真相(加冕禮的步驟并非位于認知維度上),而是指它不符合公認或通行的加冕規范,在人們看來有些怪甚至無法接受而已,所以屬于“unrichtig,wrong”而非“falsch,false”的范疇。嚴格說來,這種用“錯(不正當)”表達的價值評判與我們指責加冕禮中某人的行為“虛假”或“虛偽”也有所不同,因為后者主要意味著此人的行為沒有“真實”或“真誠”地表達他的內心情感,哪怕這種行為一絲不茍地完全符合公認或通行的加冕規范[2](P347-348)。就此而言,后期維特根斯坦似乎還是未能辨析“正確”一詞在不同語境里的不同含義,尤其沒有注意到它雖然總是具有“符合標準”的核心語義,卻又會因為“符合”的標準不同而出現質的分化這個關鍵的問題。
綜上所述,雖然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為我們理解不同于認知正確和邏輯正確的言行正確提供了某些頗有啟發意義的洞見,但由于他未能訴諸需要(包括認知需要和非認知需要)的中介效應解決怎樣把事實與價值聯結起來的難題,也沒有具體分析認知、邏輯和言行的互動關系,僅僅滿足于圍繞語言游戲的“家族相似”展開散亂籠統、語焉不詳的跳躍式評述,卻不愿下功夫深入探究三種“正確”的“家族相似”到底是在哪些方面相同,又在哪些方面相異,結果就讓這些洞見淹沒在了一堆隨興而發的玄妙漫談中,反倒失去了前期哲學在種種漏洞中依然顯露出來的細密嚴謹的論證力度,當然也談不上幫助我們深入解答那些與三種“正確”的互動關系直接相聯的現實問題了:如果說克隆人的高科技理論在認知和邏輯上都是正確的因而可以接受,為什么它在道德上卻偏偏是不正確的因而不可接受,甚至要是有人付諸實施了,還應當對他施加令他不快的懲罰呢?毋庸諱言,在日常生活中,像這樣同時涉及三種不同意思上的“正確”之間關系的棘手問題,常常給我們帶來極大的理論挑戰和實踐困擾。有鑒于此,我們今天顯然應當對維特根斯坦有關三種“正確”的復雜見解采取學理性的分析批判態度,一方面指出他的重要貢獻,另一方面揭示他陷入的內在悖論,努力找到符合事實的認知正確、符合法則的邏輯正確和符合規范的言行正確如何在交織滲透中緊密相關的根本機制,從而為我們實際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棘手問題提供富有成效的可行方案。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