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張大千作為最早臨摹敦煌壁畫且享有世界聲譽(yù)的繪畫大師,其藝術(shù)風(fēng)格的成熟及定型深受敦煌壁畫之滋養(yǎng)。今人輯錄的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畫語(yǔ)囊括了這位藝術(shù)大師對(duì)敦煌壁畫最為全面和深入的認(rèn)識(shí)與思考,成為研究其敦煌藝術(shù)思想最為重要的文本材料。張大千畫語(yǔ)中對(duì)敦煌壁畫的畫史價(jià)值、藝術(shù)源流“本土說(shuō)”、歷代風(fēng)格、特點(diǎn)及影響方面的論述與主要觀點(diǎn),對(duì)當(dāng)下敦煌學(xué)的研究及中國(guó)畫壇的發(fā)展走向仍有啟發(fā)及參照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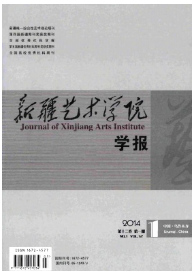
李慧國(guó), 新疆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9-03
關(guān)鍵詞:張大千 敦煌壁畫 藝術(shù)思想 張大千畫語(yǔ) 本土西行
張大千是近代以來(lái)享有世界性聲譽(yù)的繪畫大師,也是第一位遠(yuǎn)赴西北臨摹敦煌壁畫的中國(guó)畫家。也正是他在1940年代初的“西行求法”,成就了其后半生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并掀起了近代中國(guó)美術(shù)史上“本土西行”的浪潮,拉開了中國(guó)美術(shù)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序幕。張大千對(duì)敦煌壁畫的學(xué)習(xí)心得和藝術(shù)思想,不僅體現(xiàn)在其專門性的畫語(yǔ)論述中,而且也蘊(yùn)含在他后半生的繪畫實(shí)踐中,尤其是從敦煌“面壁”歸來(lái)以后所形成的畫面筆墨、線條、色彩、題跋等藝術(shù)語(yǔ)匯中。可以說(shuō),中年以后的張大千畫風(fēng)無(wú)不折射出他對(duì)敦煌藝術(shù)的理解與吸收,處處閃爍著他博大而厚重的敦煌藝術(shù)思想之光。但縱觀學(xué)界對(duì)張大千藝術(shù)思想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其作品探討繪畫美學(xué)思想的研究甚多,而專注于其畫語(yǔ)解讀個(gè)人藝術(shù)思想的研究則甚少。張大千對(duì)敦煌壁畫多方面的思考是其一生藝術(shù)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后半生藝術(shù)成熟期的主要理論源泉,他曾自言受益終身,這些思考滋潤(rùn)并哺育了最具風(fēng)格的大千繪畫藝術(shù)。因此,全面而深入地厘清張大千論敦煌壁畫的畫語(yǔ)中所蘊(yùn)含的藝術(shù)見解和個(gè)人觀點(diǎn),對(duì)客觀準(zhǔn)確地研究張大千藝術(shù)思想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和重大意義。本文將學(xué)術(shù)關(guān)注的著眼點(diǎn)落在張大千自敦煌歸來(lái)以后所發(fā)表的關(guān)于敦煌壁畫的畫語(yǔ)文獻(xiàn)上,通過(guò)全面梳理、深入解讀畫語(yǔ)文本,來(lái)系統(tǒng)總結(jié)張大千畫語(yǔ)所蘊(yùn)含的敦煌藝術(shù)思想的巨大成就。
一、張大千畫語(yǔ)中的敦煌壁畫專論
張大千自 1941 年 5 月初離開四川至 1943 年 10月末返回成都,其敦煌之行歷時(shí)2年6個(gè)月。 ①?gòu)埓笄нh(yuǎn)赴敦煌的“西行求法”成果不僅體現(xiàn)在其歷盡艱辛臨摹所得的數(shù)百卷敦煌壁畫中,也體現(xiàn)在其對(duì)敦煌壁畫的記錄整理文稿和專門論述文獻(xiàn)中。張大千對(duì)敦煌藝術(shù)遺存的記錄整理主要在《莫高窟記》(又說(shuō)謝稚柳所作)一書中,但其對(duì)敦煌藝術(shù)的個(gè)人見解及獨(dú)到認(rèn)識(shí)全部體現(xiàn)在后續(xù)由他人整理的張大千書畫題跋、畫展畫集序言、展覽講話發(fā)言、與門人子侄的談話或記者專訪、見諸報(bào)端的文字材料中,這一批材料成為張大千最全面地專論敦煌壁畫之語(yǔ)要,亦是張大千最主要的敦煌藝術(shù)研究成果。這些畫語(yǔ)文獻(xiàn)包含了張大千對(duì)敦煌藝術(shù)最為全面和系統(tǒng)的獨(dú)到認(rèn)識(shí),唯有將其精讀細(xì)研才能深入探究、體悟作者蘊(yùn)含其中的豐富而廣博的敦煌藝術(shù)思想。只有準(zhǔn)確理解張大千所汲取的敦煌藝術(shù)精髓,才能全面感知張大千滲透到作品中的傳統(tǒng)藝術(shù)精神,才能更有利于全面解讀張大千繪畫作品中的美學(xué)思想與精神內(nèi)涵。
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畫語(yǔ)多由時(shí)人根據(jù)談話整理發(fā)表在1944年的民國(guó)報(bào)刊媒介上,如《張大千話說(shuō)敦煌壁畫》《張大千談敦煌石室》《大千話敦煌》《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序言》,以及后來(lái)由其故友、門人子侄根據(jù)張大千的談話內(nèi)容回憶整理、發(fā)表或出版的文字材料中,如《張大千談敦煌壁畫》(曾克耑整理)、《張大千敦煌行》(張心智著)、《張大千的世界》(謝家孝著)等。這些材料被今人李永翹詳細(xì)分揀、整理后編入其1992 年出版的《張大千畫語(yǔ)錄》(海南攝影美術(shù)出版社)一書之第四部分“論敦煌壁畫”。第四部分的具體內(nèi)容包含:“敦煌壁畫之價(jià)值、敦煌藝術(shù)是我們中國(guó)自己的、敦煌壁畫不是工匠畫、敦煌壁畫之特點(diǎn)、敦煌壁畫對(duì)中國(guó)畫之影響、敦煌文物被毀損之真相、如何臨摹壁畫”七個(gè)專題,共計(jì)約三萬(wàn)字,成為現(xiàn)今最為完備的張大千論述敦煌壁畫的專門畫語(yǔ)②。細(xì)讀這些珍貴的畫語(yǔ)材料,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七個(gè)專題其實(shí)是張大千分別從藝術(shù)價(jià)值、藝術(shù)源流、畫家地位、文化特點(diǎn)、畫史影響、文物保護(hù)、臨摹研究七個(gè)方面對(duì)敦煌壁畫藝術(shù)所作的最為全面的專題論述,同時(shí)也是國(guó)人最早對(duì)敦煌藝術(shù)開展的理論研究,是我國(guó)敦煌學(xué)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將對(duì)此七個(gè)專題逐次論述。
(一)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價(jià)值
其一,張大千對(duì)敦煌歷代壁畫之藝術(shù)風(fēng)格作了簡(jiǎn)明扼要的點(diǎn)評(píng)。“壁畫造詣,言人像盛唐用筆雄渾,高遠(yuǎn)極峰。每一時(shí)代人民情緒,亦可考見。北魏喜夸張,畫多夸大……開(元)天(寶)而后,天下大亂,畫多草率。宋尚禮學(xué),畫法拘謹(jǐn),類今圖案畫,人像亦干枯,不及唐人豐滿,行筆用色,各不相同。”“兩魏疏冷,林野氣多;隋風(fēng)拙厚,窾奧漸啟;馴至有唐一代,則磅礴萬(wàn)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躡步晚唐,漸漸蕪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窮也。西夏諸作,雖刻劃板鈍,頗不屑踏陳?ài)E,然以較魏、唐,則勢(shì)在強(qiáng)弩也。”①縱觀敦煌壁畫的風(fēng)格面貌,北魏多見大色塊平涂,線條粗獷,人物造型簡(jiǎn)約而豪放;盛、中唐人物造型豐腴飽滿,線條飄逸穩(wěn)健,設(shè)色凝厚純正,畫風(fēng)熱烈而明快;宋代和西夏時(shí)的人物畫則清穎羸弱,線條勻細(xì)綿軟,刻畫板滯,設(shè)色沉穩(wěn)淡雅,畫風(fēng)工致而拘謹(jǐn)。由此可知,一部敦煌壁畫史就是一部中國(guó)繪畫史。
其二,張大千盛贊敦煌藝術(shù)集大成之價(jià)值。他認(rèn)為敦煌壁畫是集我國(guó)古代美術(shù)之大成,“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繼作,實(shí)先跡之奧府,繪事之神皋!”②是一千多年來(lái)中國(guó)美術(shù)史的縮影,佛教美術(shù)史上最為杰出、最為精彩的華章,乃至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跡。張大千同時(shí)也認(rèn)為敦煌之雕塑藝術(shù)極富自然之美,毫無(wú)做作,肌肉畢呈,栩栩如生。敦煌不僅有自六朝到宋元的各朝代壁畫、泥塑,而且風(fēng)格各異,內(nèi)容豐富,恰似一個(gè)大型博物館,張大千稱其為國(guó)內(nèi)最大的藝術(shù)寶庫(kù),遠(yuǎn)勝龍門、云岡等處。
其三,張大千指出了敦煌壁畫的民俗學(xué)研究?jī)r(jià)值。他認(rèn)為尤其是供養(yǎng)人畫像因保存了各個(gè)時(shí)代的服飾裝束特征及各朝人物的體貌特征而彌足珍貴。張大千高度評(píng)價(jià)敦煌文化“不僅為中國(guó)文化,且為世界文化”③。張大千很早就注意到人們對(duì)敦煌壁畫的研究大多著眼于佛像而忽視了對(duì)供養(yǎng)人像的關(guān)注,其實(shí),供養(yǎng)人像因多為對(duì)人寫像而深具“時(shí)代鱗比,秩序井然”④的寫實(shí)價(jià)值。正因如此,供養(yǎng)人形象也成為敦煌壁畫斷代研究的可靠資料。張大千甚至認(rèn)為可以根據(jù)敦煌壁畫所繪之人物形象考究歷代的服飾制度,以補(bǔ)充史書記載之不足,其以圖證史的文獻(xiàn)價(jià)值甚至可以超過(guò)藝術(shù)審美價(jià)值。
(二)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民族性
張大千始終堅(jiān)持敦煌壁畫是源自華夏本土的藝術(shù)結(jié)晶,是我們中國(guó)人自己的偉大藝術(shù)遺產(chǎn)。他在談?wù)摱鼗褪业乃囆g(shù)形式時(shí)曾說(shuō):“壁畫中之北魏及隋代者,有或謂之西洋作風(fēng),稱為犍陀羅式。然而西魏時(shí)的作風(fēng)則純屬中國(guó)式,如畫帝王后妃為中國(guó)式帝王后妃,不僅人物如此,樓臺(tái)亭榭也均為中國(guó)式。”⑤佛教繪畫在傳入西域時(shí)尚保留有濃厚的犍陀羅風(fēng)格和異域人物造型特征,在現(xiàn)今克孜爾石窟及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畫中尚能看到古代龜茲與高昌佛教藝術(shù)中的犍陀羅風(fēng)格及樣式。但是,十六國(guó)北朝時(shí)期的敦煌及河西石窟壁畫中樣式則為之一變,受中國(guó)神話及道教的影響,在石窟壁畫中大量出現(xiàn)西王母、東王公、伏羲、女媧及風(fēng)、雨、雷、電四神和飛廉、羽人等神仙形象,佛教繪畫不斷跟中國(guó)本土文化和兩漢以來(lái)的墓葬壁畫、石刻藝術(shù)相融合,吸收了不少中國(guó)傳統(tǒng)神仙信仰和道教神祇中的形象。佛、菩薩的形象也已不似龜茲石窟中那般健碩俊美,而是身材修長(zhǎng)、清瘦嫣然的“秀骨清像” 樣式。人物形象的面部特征也一改域外凹凸有致的“胡貌梵相”,變得面龐清瘦、眉目開朗。佛裝服飾也已不再是通肩式大衣或袒右肩袈裟,那種斜披外衣極富立體感的犍陀羅樣式和“曹衣出水”般的秣菟羅樣式在敦煌石窟的早期壁畫中就已經(jīng)變成了寬袍大袖、裙裾飛揚(yáng)的“褒衣博帶”式風(fēng)格。尤其是飛天的造型已經(jīng)深受漢文化中羽人、天人圖像的影響,完全改變了犍陀羅造像中身長(zhǎng)翅膀的乾闥婆、緊那羅和西域諸石窟壁畫中略顯健壯板滯的飛天造型,而是衣帶飄舉、滿壁飛動(dòng)的漢地飛天形象,及至隋唐,愈顯女性形體的婀娜多姿和舒展飄逸的靈動(dòng)氣質(zhì)。因此,佛教藝術(shù)一經(jīng)傳入漢地即與中國(guó)本土文化相融合,同時(shí)從中原傳來(lái)的新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很快就在敦煌壁畫中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影響,造就了燦爛輝煌、厚重廣博的敦煌壁畫藝術(shù),成為中國(guó)本土藝術(shù)文化中的瑰寶。張大千在印度游歷多年,親自實(shí)地考察、觀摩和研究印度石窟藝術(shù)后,仍然堅(jiān)定地認(rèn)為:“以前常有人說(shuō),中國(guó)文化多受西方影響。我研究了敦煌壁畫之后,認(rèn)為此說(shuō)不足信……佛教固然是由印度傳入,但敦煌的藝術(shù),卻是我們歷代藝術(shù)家融合貫通后的偉構(gòu),是我們中國(guó)人自己的藝術(shù)!絕不是模仿來(lái)的!”①在與謝家孝的談話中,張大千分別從透視法則、繪畫工具、人物衣冠、寶塔建筑等幾個(gè)方面例證了敦煌壁畫與印度佛教壁畫的不同之處,進(jìn)一步闡明了敦煌壁畫藝術(shù)的本土化、民族性問(wèn)題,重申了敦煌藝術(shù)源流“本土說(shuō)”。②
(三)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畫家地位
張大千認(rèn)為,從北魏到元代的壁畫唯敦煌獨(dú)盛,畫史上唐宋時(shí)期的名家大多擅長(zhǎng)繪制壁畫,不擅壁畫者,多無(wú)盛名,這些行家里手畫法亦自成一家,絕少模仿。敦煌為歷代之盛域,鑿洞供佛者非富即貴,皆競(jìng)請(qǐng)名家畫壁,名家圣手也都以在敦煌畫壁為榮。因此,張大千認(rèn)為敦煌壁畫斷然不可能是普通工匠所繪,而是多出名家之手,只是未能留下款題而已。張大千甚至認(rèn)為唐代敦煌畫壇的盛況毫不遜色于民國(guó)時(shí)期的上海。大千先生還從五個(gè)方面論證了自己的觀點(diǎn):第一,在佛畫盛行時(shí)期,凡畫佛像一定要請(qǐng)高手名家來(lái)做此莊嚴(yán)工作;第二,畫史所載的歷代畫佛名手眾多;第三,佛畫神圣莊嚴(yán),要求高,唯名家圣手方能勝任;第四,開窟崇佛盛行,仕宦商賈爭(zhēng)相聘請(qǐng)高手作畫;第五,古代敦煌乃中西交通之要道,中外具瞻,名家云集,不乏佛畫能手。張大千認(rèn)為,古代敦煌的這批畫家僅憑借著佛經(jīng)里面所記載的故事就能在荒郊石壁上創(chuàng)作出如此巨大、復(fù)雜而又生動(dòng)的畫面,有些畫面線條數(shù)尺之長(zhǎng),流貫而下,有些人物距地不足英尺亦不得失真,如果畫家不懂佛學(xué)歷史,沒(méi)有極其豐富的想象力和超乎尋常的繪制技巧,是無(wú)論如何也不可能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
(四)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四大特點(diǎn)”
張大千認(rèn)為敦煌壁畫最顯著之特點(diǎn)有四:第一,規(guī)模宏大。歷經(jīng)千年,敦煌莫高窟現(xiàn)存洞窟依然有735窟(含北區(qū))之多,依山鑿窟、櫛比鱗次,上下數(shù)層分布于崖壁,綿亙?nèi)镏b。自魏迄元,形成巨大規(guī)模,唐宋木構(gòu)飛檐翹角,遺存彩塑 2400多身,壁畫4.5萬(wàn)多平方米,這是何等宏大的文化遺產(chǎn)!第二,技巧的遞嬗。在“西行求法”期間,張大千不僅作為畫家親率門人臨摹了數(shù)百幅敦煌壁畫,而且從美術(shù)史家的視角對(duì)歷代畫風(fēng)、技巧之嬗變進(jìn)行了審視與思考。他認(rèn)為兩魏率野,隋畫溫醇,唐畫富麗,宋畫清勁,夏元板滯,這是中國(guó)藝術(shù)從進(jìn)步到衰退的自然過(guò)程,與社會(huì)風(fēng)氣有關(guān)。第三,包孕的精神。張大千認(rèn)為在新印刷術(shù)還未發(fā)明以前,字帖還可以翻印、捶拓,至于繪畫的翻印是毫無(wú)辦法的,若想看到大量古畫名跡是件很困難的事,而敦煌壁畫卻給我們呈現(xiàn)了數(shù)以千計(jì)的歷代古畫珍品。這些作品,“以時(shí)代論,便經(jīng)過(guò)北魏、西魏、隋、唐、五代、西夏等六七個(gè)朝代;以畫手論,不管是北方、南方、中國(guó)、外國(guó),無(wú)所不有;以畫派論,那么人物、花木、樹石、宮室、舟車等更是無(wú)所不備”③。第四,保存得所。大千先生認(rèn)為由于朝代更迭和戰(zhàn)亂紛爭(zhēng),加之水火、蟲蝕等病害,古代杰出的文化藝術(shù)作品得以傳世者寥若晨星,這對(duì)文化史來(lái)說(shuō)是一種無(wú)可彌補(bǔ)的損失。但敦煌石窟地處偏僻,氣候干燥,不成想竟保存下數(shù)百洞窟浩瀚的古代壁畫及彩塑藝術(shù)珍品,如果這些洞窟是在通都大邑,恐怕早就化為劫灰了!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四大特點(diǎn)”精準(zhǔn)到位,對(duì)準(zhǔn)確定義敦煌壁畫的文化價(jià)值有重要意義。四大特點(diǎn)簡(jiǎn)言之為:宏大、遞嬗、精博、得所,分別從規(guī)模、風(fēng)格、內(nèi)容、保護(hù)四個(gè)方面準(zhǔn)確概括了敦煌壁畫的四大優(yōu)勢(shì),對(duì)我們?nèi)嬲J(rèn)識(shí)敦煌藝術(shù)的文化價(jià)值有莫大幫助。
(五)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十大影響”
張大千認(rèn)為敦煌壁畫對(duì)于中國(guó)畫壇有十大影響。這十大影響分別是:一,佛像、人像畫的抬頭。二,線條被重視。三,勾染方法的復(fù)古。第四,使畫壇的小巧作風(fēng)變?yōu)閭ゴ蟆5谖澹旬媺钠埡?jiǎn)之風(fēng)變?yōu)榫芰恕5诹瑢?duì)畫佛與菩薩像有了精確的認(rèn)識(shí)。第七,女人都變?yōu)榻∶馈5诎耍嘘P(guān)史實(shí)的畫走向?qū)憣?shí)的路上去了。第九,寫佛畫卻要超現(xiàn)實(shí)來(lái)適合本國(guó)人的口味了。第十,西洋畫不足以駭?shù)刮覈?guó)的畫壇了。這十大影響實(shí)際上也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中國(guó)畫壇所欠缺的十個(gè)方面:一要重視人物畫的畫科地位;二要突出筆墨價(jià)值;三要崇尚勾染設(shè)色的厚重之美;四要崇尚宏大氣質(zhì);五要推崇精巧縝密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六要倡導(dǎo)考證,尊重客觀歷史;七要崇尚陽(yáng)剛雄健之美;八要推崇寫實(shí)風(fēng)格;九要貼近時(shí)代,表現(xiàn)中國(guó)之美;十要文化自信抵制崇洋媚外。敦煌壁畫之“十大影響”對(duì)當(dāng)下中國(guó)畫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方向仍然具有深遠(yuǎn)啟迪。
(六)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文物保護(hù)
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yàn)槎鼗筒粌H在藝術(shù)上有我國(guó)北朝及隋唐宋元塑像繪畫,而佛經(jīng)、道家經(jīng)典、儒家經(jīng)典乃至摩尼教、景教經(jīng)典等世上所未見之秘本或不傳之書籍、或已絕跡之文字,敦煌石室皆寶藏豐富。”①自清光緒二十六年農(nóng)歷四月二十七日 ② (公元1900年5月25 日)藏經(jīng)洞被發(fā)現(xiàn)以來(lái),先后有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guó)人伯希和與道士王圓箓盜賣藏經(jīng)文物,其散佚者,僅民間少數(shù)而已。敦煌石室所遭劫難還不止如此。“王道士盜賣寫經(jīng)得銀甚多,自以為功德,多將破舊佛像鏟除,另塑新像,將舊佛像堆成一塔,于宣統(tǒng)二年立碑曰“敦煌千佛洞千佛塔”,使古代珍品,遭此慘劫……前者白俄七百,住于洞內(nèi),毀壞尤兇;佛面被毀,佛身之金被刀刮去。”③ 美國(guó)人華爾納用膠布粘盜千佛洞壁畫,至今洞中殘跡壘壘。這些經(jīng)卷、塑像、壁畫被外人盜竊、損壞,是敦煌石窟藝術(shù)寶庫(kù)最大的損失。早在1941年10 月,監(jiān)察院長(zhǎng)于右任前來(lái)視察河西時(shí),張大千就曾建議由政府出面保護(hù)敦煌千佛洞遺產(chǎn):“我張大千是一個(gè)小小百姓,只是為了追求藝術(shù)事業(yè)而四處奔波,你是政府要員,有責(zé)任出來(lái)為保護(hù)我們祖先創(chuàng)造的豐富燦爛的文化遺產(chǎn)說(shuō)幾句話啊!”④ 張大千晚年雖旅居海外,但每有記者采訪,必重申敦煌石室之保護(hù)事業(yè)。
(七)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之臨摹
張大千在探討敦煌壁畫的畫語(yǔ)中談到最多的是如何臨摹敦煌壁畫的問(wèn)題。張大千自始至終都是抱著一種虔誠(chéng)崇敬的態(tài)度在臨摹敦煌壁畫,他親率門人子弟清理洞窟淤沙,為石窟編號(hào),在缺吃少用的艱苦條件下,從青海聘請(qǐng)喇嘛畫師制作畫布、顏料,輔助臨摹工作。因多數(shù)洞窟的采光不夠,張大千及其弟子均需秉燭臨摹,或立懸梯之側(cè),或臥地面之上,清晨即作,薄暮才歸,甚是辛苦。壁畫大部分畫面色彩斑駁,臨摹前須要考證年代,還原色彩,仔細(xì)觀摩研究數(shù)日才能落筆著色。張大千曾對(duì)謝家孝介紹當(dāng)初臨摹的情景:“壁畫色多斑斕,尚須秉燈靜觀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線條,我主要在觀摩揣測(cè)上下功夫,往往要數(shù)十次觀研之后才能下筆。”①
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摹始終秉持四大理念:畫材考究,一絲不茍,考證還原,形神兼顧。張大千要求巨幅畫布的縫合要涂抹膠粉三次,再用大卵石細(xì)磨七次,使布面光滑如鏡、天衣無(wú)縫。為使畫色歷久不褪,張大千團(tuán)隊(duì)多選用礦物顏料,并雇傭兒童細(xì)細(xì)研磨,所用畫紙也在四川請(qǐng)專人訂做,畫材原料極其考究。在人物造型描摹和設(shè)色處理上,張大千要求弟子們務(wù)必做到一絲不茍。他曾說(shuō):“臨摹壁畫的原則,是完全要一絲不茍地描,絕對(duì)不能參入己意,這是我一再告訴門生子侄們的工作信條。”②每一處的尺寸、色彩都要標(biāo)記清楚,在臨摹中做到不參己意,與原作一致。對(duì)于壁畫上線條漫漶、色彩墨黑之不可辨處,大千先生要求門人仔細(xì)觀研,考證其年代風(fēng)格樣貌,通過(guò)比較還原畫面本色。如佛、菩薩、飛天的服飾及發(fā)飾細(xì)節(jié)要考證清楚方可下筆,萬(wàn)不可照貓畫虎、妄加臆測(cè)。張大千還要求弟子們臨摹時(shí)不僅要準(zhǔn)確描摹出人物外形,還要完整傳達(dá)出人物神情,不僅要做到形似,更要追求神似,無(wú)論形神都要細(xì)細(xì)領(lǐng)會(huì)。 “譬如,壁畫中的佛像肅穆端莊,菩薩慈祥可親,飛天秀麗活潑,天王、力士威武雄壯。但是,肅穆端莊不是呆板,秀麗活潑不是輕浮,威武雄壯不是兇惡,這些都是需要認(rèn)真仔細(xì)觀察研究的。”③張大千還經(jīng)常給門人強(qiáng)調(diào)臨摹的重要性,勸誡弟子只有通過(guò)臨摹方能掌握古畫之規(guī)律,才可借前人之長(zhǎng)參入自我心得,寫出心中意境,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作品。
二、張大千畫語(yǔ)中的敦煌藝術(shù)思想成就
(一)首次論述了敦煌壁畫的歷史價(jià)值。
張大千是國(guó)內(nèi)系統(tǒng)研究敦煌壁畫的第一人,他首次論述了敦煌壁畫的歷史價(jià)值。其一,敦煌壁畫內(nèi)容豐富,造型精美,勾染精妙,極富自然之美且絢燦多姿,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其二,敦煌壁畫規(guī)模宏大,包孕萬(wàn)象,集古代繪畫之大成,呈歷代風(fēng)格之嬗變,具有極高的畫史研究?jī)r(jià)值。其三,敦煌壁畫求真寫實(shí),反映社會(huì)風(fēng)俗史實(shí),具有極高的民俗史學(xué)價(jià)值。正是張大千從理論層面對(duì)敦煌壁畫的價(jià)值進(jìn)行論述,以及從視覺(jué)層面對(duì)敦煌壁畫進(jìn)行臨摹,才使得國(guó)民大眾在那個(gè)落后、封閉的年代里,對(duì)遺存在西北的敦煌壁畫藝術(shù)有了全面的認(rèn)識(shí)和價(jià)值判斷。也正是張大千深諳敦煌壁畫的歷史價(jià)值,多次呼吁政府成立專門機(jī)構(gòu)用以對(duì)敦煌石窟藝術(shù)的保護(hù)與研究,才有了后來(lái)的國(guó)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如今,敦煌石窟已得到國(guó)家的高度重視和妥善保護(hù),敦煌學(xué)也已成為一門國(guó)際性“顯學(xué)”,備受世界各地研究學(xué)者的關(guān)注。也是由于張大千洞曉敦煌壁畫所蘊(yùn)藏的傳統(tǒng)價(jià)值,才掀起了中國(guó)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的民族復(fù)興浪潮。正如當(dāng)代美術(shù)評(píng)論家林木先生所言:“作為畫家的張大千完成了一個(gè)中國(guó)文化學(xué)者復(fù)興中華文化的偉大使命,也打破了研究中國(guó)繪畫傳統(tǒng)而丟掉了重要的宗教畫領(lǐng)域的嚴(yán)重歷史疏漏。僅憑這一點(diǎn),張大千也可馳名于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史而絕無(wú)愧色。”①
(二)全面彰顯了華夏美術(shù)的民族精神。
張大千首先嚴(yán)厲抨擊了中國(guó)文化“外來(lái)說(shuō)”的觀點(diǎn),從諸多方面論證了敦煌壁畫“本土化”觀點(diǎn),堅(jiān)定地認(rèn)為敦煌藝術(shù)是國(guó)人自己的藝術(shù),是歷代藝術(shù)家融會(huì)貫通后的偉構(gòu),絕不是模仿來(lái)的。其次,張大千從藝術(shù)語(yǔ)言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了線條與色彩在中國(guó)畫傳統(tǒng)中的重要性。他認(rèn)為,中國(guó)畫歷來(lái)講究以書入畫,線條是中國(guó)畫的靈魂。人物畫的線條追求剛勁的筆力,匠人們多不懂得線條的重要性,中國(guó)畫中的白描傳統(tǒng)也因人物畫的衰落而被世人逐漸遺棄。而敦煌壁畫中的線條卻是秀勁絕倫,滿壁飛動(dòng),猶如“鐵畫銀鉤”。敦煌壁畫中的色彩也是極具渲染之力,厚上加厚,美上加美,醇厚之余,絕不草率,這才是傳統(tǒng)中國(guó)畫固有的民族語(yǔ)言。再次,張大千從藝術(shù)形式的角度肯定了敦煌壁畫中宏大的氣勢(shì)和強(qiáng)健的形象。華夏美術(shù)自漢唐以來(lái)就始終保持著氣勢(shì)恢弘、雄偉健美、陽(yáng)剛大氣、絢爛磅礴的美學(xué)氣質(zhì),作為國(guó)粹的中國(guó)畫藝術(shù)不論在什么年代都應(yīng)始終保持這種本真的民族氣魄。最后,張大千從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角度贊揚(yáng)了敦煌壁畫中的精密態(tài)度和寫實(shí)風(fēng)格。中國(guó)畫也并非一開始就崇尚寫意簡(jiǎn)約,唐宋名家多尚精細(xì)之畫風(fēng),人物畫如《簪花仕女圖》《韓熙載夜宴圖》等極盡寫實(shí)之精神與精密之態(tài)度。就唐宋山水畫而論,若大小李將軍、荊關(guān)董巨、李成范寬、劉李馬夏等皆是千巖萬(wàn)壑、繁復(fù)異常,精細(xì)無(wú)比。因此,逸筆草草、簡(jiǎn)古淡遠(yuǎn)并非中國(guó)畫的一貫傳統(tǒng),求真寫實(shí)、精巧縝密才是傳統(tǒng)繪畫可貴的藝術(shù)品質(zhì)。
敦煌壁畫不論是在藝術(shù)語(yǔ)言、藝術(shù)形式抑或是藝術(shù)風(fēng)格上,都與明清以來(lái)的文人畫有很大差異。就連常書鴻先生也認(rèn)為:“(敦煌畫工)他們并不留戀什么殘山剩水,也不主張什么胸中丘壑,而是切切實(shí)實(shí)地描繪社會(huì)生活和理想中的佛家世界,使人們喜聞樂(lè)見。他們的筆觸剛勁有力,線條流暢完美,美輪美奐。畫工所形成的淳樸而渾厚的畫風(fēng)與后來(lái)中國(guó)文人畫的繪畫風(fēng)格,是兩種不同的風(fēng)格和路子。我認(rèn)為這是中國(guó)藝術(shù)的正宗和主流。”② 張大千論敦煌壁畫全面彰顯了作為中國(guó)藝術(shù)的正宗和主流所蘊(yùn)含的民族精神,并且批判了近世以來(lái)中國(guó)畫過(guò)于注重筆墨、小巧、柔美、茍簡(jiǎn)、意象的風(fēng)氣,匡正了傳統(tǒng)中國(guó)藝術(shù)的審美精神,為民族繪畫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指引了方向。
(三)引領(lǐng)了中國(guó)藝術(shù)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張大千遠(yuǎn)赴敦煌臨摹壁畫的年代正值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相持階段,民族危難給中國(guó)藝術(shù)的發(fā)展帶來(lái)了沉痛的打擊,使當(dāng)時(shí)的藝術(shù)格局被迫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折,并開始重新建構(gòu)。“中國(guó)藝術(shù)界在這種文化格局的變動(dòng)中,一方面被迫從傳統(tǒng)藝術(shù)的中心區(qū)域向邊緣區(qū)域遷移,另一方面,也開始努力從原來(lái)對(duì)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理論問(wèn)題的關(guān)注轉(zhuǎn)而面對(duì)民族危亡的迫切現(xiàn)實(shí),從而開始了對(duì)西南、西北區(qū)域文化價(jià)值的發(fā)掘工作。”③此時(shí),張大千“西行求法”的壯舉在戰(zhàn)時(shí)的中國(guó)美術(shù)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dòng),猶如春雷乍響,引領(lǐng)陷入彷徨和焦灼的中國(guó)藝術(shù)家們紛紛前往祖國(guó)的西部邊陲,到那里尋覓古代藝術(shù)遺存的傳統(tǒng)語(yǔ)匯,追求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民族精神。在1941年到1945年間,政府組織的邊疆文化考察以及個(gè)人自發(fā)的西部藝術(shù)采風(fēng)均接連不斷,匯成了一股文藝界巨大的“本土西行”浪潮。如:王子云率領(lǐng)的西北藝術(shù)文物考察團(tuán),向達(dá)率領(lǐng)的西北史地考察團(tuán),謝稚柳、常書鴻、呂斯百、孫宗慰、吳作人、韓樂(lè)然、關(guān)山月、董希文、司徒喬、潘絜茲等人先后到甘肅、青海、新疆考察寫生。也正是這一批又一批的文藝志士們虔誠(chéng)地在邊遠(yuǎn)蠻荒的西部本土匍匐向前,才使得中國(guó)現(xiàn)代藝術(shù)能夠深深扎根于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強(qiáng)烈的民族意識(shí)和家國(guó)情懷。
三、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張大千論敦煌壁畫具有極高的歷史成就與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這些零散的畫語(yǔ)在當(dāng)時(shí)雖未成皇皇巨著,但它與大千先生“西行求法”的壯舉一道具有崇高之價(jià)值、撼人之魅力,它不僅首次論述了敦煌壁畫之歷史價(jià)值,全面彰顯了華夏美術(shù)之民族精神,而且自發(fā)引領(lǐng)了中國(guó)藝術(shù)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尤其是張大千對(duì)敦煌壁畫畫史價(jià)值、藝術(shù)源流“本土說(shuō)”、敦煌壁畫歷代風(fēng)格、特點(diǎn)及影響方面的論述與觀點(diǎn),對(duì)當(dāng)下敦煌學(xué)的研究及中國(guó)畫壇的發(fā)展走向有深遠(yuǎn)啟發(fā)及諸多參照,其壁畫臨摹方面的心得對(duì)當(dāng)今中國(guó)人物畫創(chuàng)作和壁畫臨摹教學(xué)亦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鑒意義。
張大千論敦煌壁畫也是我國(guó)最早的敦煌學(xué)研究成果之一,至今仍能對(duì)敦煌繪畫藝術(shù)的研究產(chǎn)生多元的學(xué)術(shù)啟迪。而張大千在繪畫藝術(shù)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他對(duì)敦煌藝術(shù)進(jìn)行深入思考與研究之后所形成的傳統(tǒng)學(xué)養(yǎng),今人若能從張大千畫語(yǔ)中對(duì)博大的敦煌藝術(shù)精神悟得三分,必能提升當(dāng)下中國(guó)畫創(chuàng)作的整體水平。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wèn)題 >
SCI常見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