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作為迄今為止人類歷時(shí)最長、規(guī)模最大的國際庭審,懲治了戰(zhàn)犯,彰顯了正義,定義了戰(zhàn)后國際格局,重要性不言而喻,對(duì)其進(jìn)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及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但長期以來學(xué)者對(duì)其研究重視程度卻不如同時(shí)代的紐倫堡審判,更遑論對(duì)審判中翻譯問題的研究。口譯對(duì)庭審的順利進(jìn)行、確保對(duì)戰(zhàn)犯進(jìn)行公平、公開、公正的審判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本文主要探析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口譯制度,分析歷史背景、法律依據(jù)。最后總結(jié)其對(duì)研究二戰(zhàn)史及口譯史的重要意義,指出技術(shù)對(duì)語言服務(wù)的積極影響,以及語言能力對(duì)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戰(zhàn)略意義。
關(guān)鍵詞: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審判;口譯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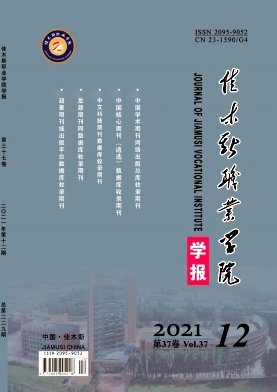
黃旦華-《佳木斯職業(y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1年5期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法西斯宣布無條件投降,標(biāo)志著二戰(zhàn)結(jié)束。根據(jù)《開羅宣言》《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相關(guān)協(xié)議及文件,同盟國決定對(duì)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的主要戰(zhàn)犯進(jìn)行審判,因?qū)徟性跂|京進(jìn)行,所以俗稱東京審判。截至 2021 年 1 月 1 日,在中國知網(wǎng)中輸入“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按照篇名進(jìn)行檢索,共檢索到 85 條文獻(xiàn);輸入 “東京審判”按照篇名進(jìn)行檢索,共檢索到 542 條文獻(xiàn)。由此可以看出,在研究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時(shí)多數(shù)學(xué)者使用“東京審判”。本文作者使用其正式名稱“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以下簡稱“庭審”)。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于 1946 年 4 月 29 日召開,會(huì)議決定對(duì)日本的領(lǐng)導(dǎo)人進(jìn)行審判,指控他們共謀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
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美軍登陸日本先后四次總共逮捕 100 多名戰(zhàn)犯,其中包括 28 名甲級(jí)戰(zhàn)犯,1 人因精神問題、2 人因病亡而免于審判,其余 25 名罪犯全部被判有罪。東條英機(jī)等 7 名甲級(jí)戰(zhàn)犯被判處絞刑,16 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 人被判處 20 年有期徒刑,1 人被判處 7 年有期徒刑[1]。庭審模式基本援用了紐倫堡審判模式,兩者都采用英美法程序進(jìn)行審判[2],但是兩者又有許多不同之處。紐倫堡審判主要由美、蘇、英、法主導(dǎo),庭審過程中出現(xiàn)的重大問題基本都是四國協(xié)商解決的,而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主要是由美國主導(dǎo)的。
一、庭審翻譯概述
(一)庭審口譯的法理依據(jù)
《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第 1 節(jié)第 3 條對(duì)秘書處的組成有詳細(xì)說明。The Secretariat of the Tribunal shall be composed of a General Secretaryto be appointed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and such assistant secretaries,clerks,interpreters,and other personnel as may be necessary.(法庭秘書處應(yīng)由盟軍最高司令任命一名秘書長和必要的助理秘書、書記員、口譯員和其他人員組成);第 3 節(jié)第 9 條對(duì)翻譯做出了如下規(guī)定。Procedure for Fair Trial.In order to insure fair trial for the accused,the following procedure shall be followed:C.Language.The trial and related proceedings sha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ccused. Translations of documents and other papers shall be provided as needed and requested.(為了確保對(duì)被告進(jìn)行公正審判,應(yīng)遵循以下程序:語言,審判及相關(guān)的訴訟應(yīng)以英語及被告語言進(jìn)行,應(yīng)根據(jù)需要及請(qǐng)求提供文件和其他資料的翻譯)。憲章中直接有兩條提到了口譯人員及筆譯,另外一條提到所有起訴狀包括憲章副本應(yīng)以被告能夠理解的語言提供給他們。由此可見,為了保證被告的權(quán)利,憲章明文規(guī)定了法庭庭審口譯以英語和日語進(jìn)行,并規(guī)定了在庭審過程中應(yīng)提供相應(yīng)的筆譯服務(wù)。
(二)庭審口譯制度
法庭在庭審口譯中采用了三級(jí)制:日本人、日裔美國人及美國白人。口譯員都是日本人,他們?cè)谌毡境錾邮芙逃皇菍I(yè)譯員沒有法庭口譯經(jīng)驗(yàn);監(jiān)聽員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被稱為“二世”,他們?cè)诿绹錾谌毡鹃L大并接受教育,二戰(zhàn)前回到美國,二戰(zhàn)期間為盟軍翻譯部服務(wù),具備良好的日英雙語能力,通曉日本文化歷史,在庭審中負(fù)責(zé)監(jiān)督翻譯并確保英文翻譯的質(zhì)量;語言仲裁官則是美國白人軍官,負(fù)責(zé)裁決翻譯過程中產(chǎn)生的語言爭(zhēng)議。法庭共有 27 名口譯員,4 名監(jiān)聽員, 2 名語言仲裁官。從社會(huì)地位及政治權(quán)力來看,最底層是日本口譯員,中間層是日裔美國人,最上層是美國白人。但從語言能力來看卻完全相反,作為仲裁官的美國白人日語水平最低,擔(dān)任監(jiān)聽員的日裔美國人日語水平居中,擔(dān)任口譯員的日本人日語水平最高,導(dǎo)致他們語言能力與話語權(quán)力的倒置。
第一,譯員選拔。庭審中聘請(qǐng)的口譯員都是日本人,沒有同盟國的口譯員,最主要的原因是二戰(zhàn)以前西方社會(huì)其實(shí)對(duì)日本文化尤其是日語并不重視,短期內(nèi)無法快速培養(yǎng)數(shù)量充足勝任庭審口譯的日語翻譯人才。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決定聘用日本人擔(dān)任法庭口譯員。當(dāng)時(shí)物色精通日語和英語、了解日本歷史文化、通曉法庭術(shù)語且具有法庭翻譯經(jīng)驗(yàn)的口譯員是極其困難的,因此具備良好的英語水平就成了法庭選拔口譯員的唯一重要標(biāo)準(zhǔn)。正式開庭前,法庭進(jìn)行了模擬審判來選拔口譯員,候選口譯員要翻譯法官、檢察官、律師的陳述,而其他候選口譯員則在法庭扮演其他出庭者的角色,通過測(cè)試法庭將聘請(qǐng)其在被法庭語言服務(wù)部擔(dān)任翻譯。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遴選過程因缺乏合格的口譯員而受到更大限制。因此,選拔要求不像紐倫堡審判那樣嚴(yán)格,幾乎不需口譯經(jīng)驗(yàn)。
第二,口譯模式。庭審也采用了在紐倫堡審判中配有的 IBM 系統(tǒng)譯員箱。庭審中所有人都佩戴耳機(jī),陳述時(shí)對(duì)著麥克風(fēng),翻譯系統(tǒng)有兩個(gè)頻道,英語和日語。該系統(tǒng)在紐倫堡審判中證明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在庭審中,由于英語和日語在文化和句法上的巨大差異,適合紐倫堡審判的同聲傳譯并不適合用于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這種情況下法庭最終采用了交替?zhèn)髯g的模式。一個(gè)譯員箱有兩名口譯員一起工作,一名負(fù)責(zé)英譯日,一名負(fù)責(zé)日譯英,如果一個(gè)譯員有問題,另外一個(gè)譯員會(huì)替補(bǔ),每個(gè)譯員交替工作約 30 分鐘。庭審使用兩種語言,耗時(shí)約兩年半。庭審時(shí)間過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gè)重要原因就是庭審口譯模式的問題,因?yàn)榻惶鎮(zhèn)髯g會(huì)比同聲傳譯花費(fèi)更長的時(shí)間。
第三,監(jiān)聽員與語言仲裁官的角色。法庭總共有 4 名監(jiān)聽員,都屬于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語言服務(wù)部。庭審中他們的職責(zé)包括檢查并糾正不當(dāng)或錯(cuò)誤的翻譯,還包括在法庭宣讀一些重要文件,比如,翻譯成日語的起訴書和判決。每天庭審前,監(jiān)聽員負(fù)責(zé)告訴口譯員案情摘要,安排口譯工作,決定負(fù)責(zé)英譯日及日譯英的口譯員。庭審監(jiān)聽員還為口譯員提供幫助,比如,幫助譯員記下像日期和時(shí)間段這樣的細(xì)節(jié)信息。如果檢察官、律師、證人的陳述過于冗長,監(jiān)聽員會(huì)亮起發(fā)言席上的紅燈讓他們停止講話,讓譯員有足夠的時(shí)間理解并進(jìn)行口譯;陳述或翻譯有歧義時(shí),監(jiān)聽員會(huì)讓法庭記者大聲宣讀相關(guān)內(nèi)容,以便消除歧義。當(dāng)口譯員碰到問題或者認(rèn)為口譯員無法勝任具體工作的時(shí)候,監(jiān)聽員會(huì)安排替補(bǔ)口譯員。
語言仲裁委員會(huì)是作為解決翻譯(包含筆譯和口譯)爭(zhēng)議而設(shè)立的。當(dāng)檢方或辯方對(duì)翻譯質(zhì)疑時(shí),法庭庭長將此事交由語言仲裁官處理。在法庭經(jīng)法官協(xié)商,語言仲裁官隨后在庭審中宣布裁決。一旦仲裁委員會(huì)解決了某個(gè)有爭(zhēng)議的翻譯,那么接下來的庭審中將會(huì)使用仲裁后的翻譯。語言仲裁官由法庭任命,共有兩名,由美國軍官擔(dān)任。第一位是拉德納·摩爾少校,他父母是最早一批來到日本的美國傳教士。他出生在日本大阪,在美國上大學(xué),之后又回到日本傳教,他流暢的日語對(duì)庭審起到重要作用。摩爾退役后接替他的是克拉夫特上尉,但是資料記載他只學(xué)過一年的初級(jí)日語,實(shí)際發(fā)揮的作用有待商榷。
第四,口譯三級(jí)制的原因。不同于紐倫堡審判,庭審中的口譯采用了三級(jí)制。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在 1948 年 11 月 4 日的判決中解釋了設(shè)立語言仲裁委員會(huì)的原因:從日語直譯成英語或者反過來往往是不可能的,很大程度上,只能意譯。兩種語言的專家在宣讀翻譯時(shí)經(jīng)常碰到困難,因此法庭不得不成立語言仲裁委員會(huì)解決有爭(zhēng)議的翻譯問題。官方聲明設(shè)置語言仲裁官主要是為了解決翻譯中理解的分歧,但考慮到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政治背景、國際關(guān)系,顯然還有其他深層次的原因。一是折中妥協(xié),因無法在同盟國內(nèi)部招聘到優(yōu)秀的口譯員用于庭審,沒有譯員,庭審將無法進(jìn)行,因此被迫聘用日本人擔(dān)任口譯員。二是情感因素,完全依靠日本譯員,同盟國情感上無法接受,不想落人口實(shí),留下庭審是依靠日本人完成的印象。三是信任因素,庭審是對(duì)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顯然法庭是不可能完全信任與戰(zhàn)犯相同國籍的日本口譯員的。許多口譯員本身與被告或與日本政府有著緊密關(guān)系,多人曾是日本外務(wù)省的外交官。鑒于 28 名被告中包括 3 名外交大臣、2 名外交官和 17 名軍方領(lǐng)導(dǎo)人,這些口譯員實(shí)際上是在決定他們之前上司命運(yùn)的審判中擔(dān)任翻譯,顯然法庭不能完全信任口譯員。因此,設(shè)置了英日雙語能力較好的日裔美國人擔(dān)任監(jiān)聽員。日裔美國人雖然是美國公民,但是因?yàn)樵谔窖髴?zhàn)爭(zhēng)期間,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大量美國人掀起了排日運(yùn)動(dòng),使得這些日本人實(shí)際上在美國受到很大排擠。法庭還設(shè)置了語言仲裁官,對(duì)有爭(zhēng)議的翻譯進(jìn)行仲裁,除了進(jìn)行翻譯仲裁,仲裁官的另外一個(gè)作用就是監(jiān)督監(jiān)聽員,可以看出仲裁官的設(shè)置也是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一種權(quán)力象征。歷史上口譯員的作用主要是由他所處的權(quán)利和地位等級(jí)結(jié)構(gòu)決定的,社會(huì)政治性在庭審口譯員的結(jié)構(gòu)層級(jí)中體現(xiàn)明顯。
第五,庭審口譯的道德準(zhǔn)則。許多口譯員都曾在日本軍隊(duì)服役,庭審時(shí)不得不為他們的上級(jí)翻譯。比如,參加庭審翻譯最多的島內(nèi)敏郎,在二戰(zhàn)期間曾擔(dān)任日本外務(wù)大臣東鄉(xiāng)茂德的翻譯,與許多官員都有交集。但在庭審翻譯中非但沒有回避,反而是出庭翻譯次數(shù)最多的口譯員。因?yàn)闆]有相關(guān)的條約及文件約束庭審口譯員的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所以雖然沒有相關(guān)證據(jù)表明日本口譯員違反口譯的職業(yè)道德。但這些譯員,面對(duì)曾經(jīng)的長官,內(nèi)心必然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同樣作為二世的監(jiān)聽員,一方面他們是美國公民,另一方面他們的日本親人和朋友可能在戰(zhàn)爭(zhēng)中被盟軍俘虜關(guān)在監(jiān)獄、受傷或喪生,雙重身份也會(huì)造成心理上的阻礙。盟軍制定口譯制度時(shí)沒有考慮譯員的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從而避免身份認(rèn)同和情感因素對(duì)翻譯的公正性造成消極影響。日本右翼勢(shì)力鼓噪庭審是戰(zhàn)勝國對(duì)戰(zhàn)敗國不公平的審判,但是從庭審翻譯制度來看,口譯員均為日本人,沒有要求他們進(jìn)行利益回避,這種制度的設(shè)置顯然是有利于被告的,從翻譯角度來看這是對(duì)右翼謬論最直接、最有力的駁斥。
二、庭審口譯制度的當(dāng)代價(jià)值及啟示
(一)豐富二戰(zhàn)史研究及法庭口譯史研究的內(nèi)涵
不同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翻譯實(shí)現(xiàn)的,庭審主要也是通過翻譯完成的。口譯員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締造者[3]。翻譯在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庭庭審口譯作為二戰(zhàn)庭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duì)其進(jìn)行研究也是對(duì)二戰(zhàn)相關(guān)歷史的研究。通過口譯員的語言活動(dòng)還原了歷史真相,讓更多人了解真實(shí)的歷史。研究庭審翻譯有助于構(gòu)建和保存新的歷史證據(jù),證明口譯活動(dòng)如何在不同的地理和地緣政治背景下解決各種問題,以及口譯員如何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和社會(huì)文化背景下發(fā)揮作用。以不同的視角研究參與重要?dú)v史事件的口譯員及翻譯活動(dòng)豐富了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因此研究庭審翻譯對(duì)于翻譯職業(yè)與實(shí)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在歷史事件中分析翻譯活動(dòng),通過搜集、整理、分析、歸納相關(guān)歷史事實(shí),結(jié)合政治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法學(xué)、倫理學(xué)等對(duì)歷史事件進(jìn)行研究,可以拓展二戰(zhàn)歷史與相關(guān)口譯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二)推動(dòng)技術(shù)在語言服務(wù)中的運(yùn)用
庭審采用了相同的 IBM 設(shè)備,耗時(shí)卻超過兩年半。如此長的時(shí)間主要是因?yàn)橥彶捎昧藲W美法系,需要充分的證據(jù)才可以定罪,因此圍繞證據(jù)是否有效的庭審辯論環(huán)節(jié)花費(fèi)很長時(shí)間;另外,確保翻譯公平公正的三級(jí)翻譯制度,因?yàn)榉g糾錯(cuò),翻譯仲裁本身也延長了庭審的時(shí)間。可以想象如果沒有使用翻譯設(shè)備,庭審的時(shí)間將會(huì)更長。可以說當(dāng)時(shí)的紐倫堡審判和庭審定義了現(xiàn)代大型國際會(huì)議的翻譯模式,現(xiàn)在基本上所有國際會(huì)議都會(huì)提供同傳或交傳服務(wù)。人類從未停止探索將技術(shù)運(yùn)用于語言服務(wù)的腳步,從第一代基于規(guī)則的機(jī)器翻譯到現(xiàn)在第四代基于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的神經(jīng)機(jī)器翻譯,翻譯技術(shù)取得了巨大進(jìn)步。雖然圍繞機(jī)器翻譯是否可以替代人工翻譯的爭(zhēng)論從未中斷,目前來看機(jī)器翻譯還無法完全替代人工翻譯,但是采用機(jī)器翻譯、人工進(jìn)行譯后編輯的方式能夠提高翻譯的速度與質(zhì)量已是業(yè)內(nèi)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目前有多家科技公司致力于研發(fā) AI 口譯,比如,訊飛和騰訊都有他們的 AI 口譯產(chǎn)品,博鰲亞洲論壇上,都使用了 AI 同傳技術(shù)。盡管這一技術(shù)還不完善,但是任何新技術(shù)的成熟運(yùn)用都有一個(gè)過程,許多國家都很重視提高語言技術(shù)開發(fā)水平以及語言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能力。
(三)提高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中國在世界舞臺(tái)上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積極參與全球事務(wù),如在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安全、生態(tài)等各領(lǐng)域的公共事務(wù),推動(dòng)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其中一個(gè)重要的戰(zhàn)略能力就是提升話語塑造能力、提高國際話語權(quán)。而國家語言能力是一個(gè)國家處理海內(nèi)外事務(wù)所需要的語言能力。當(dāng)前國家語言能力與我國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需要強(qiáng)大的語言能力來支撐,因此也啟發(fā)我國相關(guān)學(xué)者應(yīng)該研究如何健全國家語言能力建設(shè)機(jī)制,尤其是語言服務(wù)能力包括翻譯能力。在吸收歷史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需要制定相關(guān)的語言政策,培養(yǎng)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復(fù)合型語言人才服務(wù)于國家戰(zhàn)略需要。
三、結(jié)語
研究庭審口譯制度對(duì)于研究口譯史具有重要意義,從翻譯視角對(duì)庭審進(jìn)行研究豐富了二戰(zhàn)的史料研究。本文梳理了庭審口譯的法律依據(jù)、口譯制度、口譯模式、口譯員的選拔、監(jiān)聽員和語言仲裁官的角色及三者的相互關(guān)系, 以及三級(jí)制背后的原因。庭審中將技術(shù)與翻譯融合,對(duì)于當(dāng)今將語言技術(shù)用于提高語言服務(wù)的質(zhì)量和效率有重要指導(dǎo)意義,對(duì)于我國在 21 世紀(jì)如何更好地進(jìn)行制度建設(shè)、加強(qiáng)國家的語言能力及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筆者分析的重點(diǎn)主要涉及憲章規(guī)定的兩種官方語言英語和日語的口譯,但其實(shí)在庭審中還涉及漢語、法語、俄語的翻譯。中國口譯員在庭審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也是今后研究領(lǐng)域的重點(diǎn),將會(huì)進(jìn)一步豐富二戰(zhàn)相關(guān)翻譯及史實(shí)研究。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