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在建抽蓄電站長隧洞的施工大多以爆破為主要開挖手段,爆破后產生的有毒有害氣體給施工環境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基于大渦模擬(LES)數值方法,建立了施工長隧洞空氣流動及不同氣體組分輸運的數值仿真模型,針對在建的安徽金寨抽蓄電站施工隧洞爆破后有毒有害氣體遷移規律進行仿真計算。通過現場實測數據對數值計算模型可靠性進行了驗證,得到了與實際較為吻合的氣體濃度遷移變化規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模擬了不同通風速度和不同掘進深度下的有毒有害氣體運移規律,預測了氣體停留時間。研究成果對抽蓄電站地下施工隧洞通風設計和安全施工具有指導意義。
關 鍵 詞:有毒有害氣體; 遷移規律; 大渦模擬; 地下洞室施工; 抽蓄電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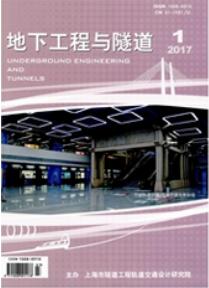
推薦閱讀:《地下工程與隧道》(季刊)創刊于1991年,是上海市隧道工程軌道交通設計研究院、上海市地鐵總公司和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辦,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協辦的技術性科技期刊。
抽蓄電站是世界公認的運行靈活而可靠的調峰電源。電網調峰削谷需要建設一定規模的抽蓄電站[1]。國內目前有多座抽蓄電站處于施工建設階段,而電站大型地下洞室在施工期間大多選擇爆破為主要開挖手段,炮煙、粉塵及汽車尾氣等均屬于有害物質,施工人員長時間暴露在這些氣體下會損害身體健康,引發職業病等[2-3]。因此,對爆破后產生的有毒有害氣體遷移規律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對地下洞室有毒有害氣體的遷移已經有了部分研究成果。南春子等采用組分輸運模型模擬地下水封隧洞有害氣體擴散,計算的有害氣體濃度隨時間變化曲線與實測值基本吻合,為組分輸運模型的正確性提供了佐證[4];李翠平等模擬了煙流在三維洞室中的動態蔓延過程,進而揭示了煙流溫度、濃度等在時間、空間上的演變,提出了煙流蔓延三維仿真模型[5]。
針對地下洞室施工與否對有毒有害氣體遷移擴散有很大影響,鄭汝松等對有毒有害氣體濃度變化進行了仿真分析,揭示了有毒有害氣體的擴散規律[6];王敏等運用FLUENT模擬軟件對地下洞室爆破后產生的有毒有害氣體的遷移進行仿真實驗,為通風設計提供了一些建議[7];王曉玲等建立了獨頭引水隧洞壓入式通風紊流三維高雷諾數k-ε數學模型,分析了不同通風時刻掘進隧洞內CO遷移和分布規律,但沒有對混合氣體進行仿真模擬[8]。由于抽蓄電站地下洞室建筑結構復雜,建立準確的數學模型預測其地下施工洞室爆破后有毒有害氣體的運移規律對水電站施工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在建安徽金寨抽蓄電站地下施工洞室為研究對象,對爆破后產生的有毒有害氣體進行大渦模擬(LES) ,建立了地下廠房不同氣體組分流動及輸運的三維仿真模型。在驗證模型可靠性的基礎上,對不同通風條件和掘進深度情況下的氣體運移規律進行計算分析。
4 結 論
抽蓄電站地下施工洞室有毒有害氣體遷移規律的研究對水電站地下廠房正常施工具有重要意義。在本文對正在施工的金寨抽蓄電站有毒有害氣體進行測量,并驗證氣體遷移數學模型準確的基礎上,對不同風速和掘進洞深工況進行仿真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 本文建立的抽蓄電站地下洞室有毒有害氣體非穩態輸運模型計算得到了與實測數據基本吻合的氣體濃度擴散規律,可用于預測施工洞室有毒有害氣體的遷移輸運規律。
(2) 有毒有害氣體在爆破后沿程遷移過程中峰值濃度逐漸下降,高濃度區域逐漸擴大。不同風速工況下,隨著通風量的增大,有毒有害氣體遷移速度隨之增加,到達同一測點所需時間減小;氣體峰值濃度越高,測點處氣體持續時間越短。
(3) 不同掘進洞深情況下,掘進洞深越淺,有毒氣體持續時間隨風速的增加而下降較快;掘進深度較深時,持續時間受風速的影響減小。同一風速下,爆破后有毒有害氣體遷移至洞口時間與掘進洞深呈線性正相關。
參考文獻:
[1] 宋晉紅,周軍,薛小兵,等.抽水蓄能電站發電機層溫度均勻性研究[J].人民長江,2018,49(15):105-110.
[2] 王敏.大型地下洞室開挖施工的通風排煙排塵過程數值仿真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4.
[3] 危寧,李力,王春燕.隧道施工通風中的有害氣體濃度變化分析[J].三峽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4):324-327.
[4] 南春子.長距離復雜洞室聯動通風與污染物擴散的數值模擬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2015.
[5] 李翠平,曹志國,李仲學,等.地下礦火災煙流蔓延的三維仿真構模技術[J].煤炭學報,2013,38(2):257-263.
[6] 鄭汝松,王紅軍,李飛,等.地下洞室通風有害氣體濃度變化分析[J].云南水力發電,2008(3):65-68.
[7] 王敏.大型地下洞室開挖施工的通風排煙排塵過程數值仿真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4.
[8] 王曉玲,陳紅超,劉雪朋,等.引水隧洞獨頭掘進工作面風流組織與CO擴散的模擬[J].水利學報,2008(1):121-127.
[9] Li L,Li B.Investigation of Bubble-Slag Layer Behaviors with Hybrid Eulerian–Lagrangian Modeling and Large Eddy Simulation[J].Journal of the Minerals,Metals & Material Socienty,2016,68(8):2160-2169.
[10] 陶文銓.數值傳熱學[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1.
[11] 蘇銘德,黃素逸.計算流體力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12] Li L,Liu Z,Cao M,et al.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Bubbly Flow and Slag Layer Behavior in Ladle with Discrete Phase Model (DPM)–Volume of Fluid (VOF) Coupled Mode[J].Journal of the Minerals,Metals & Material Socienty,2015,67(7):1-9.
[13] 王婷婷,楊慶山.基于FLUENT的大氣邊界層風場LES模擬[J].計算力學學報,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