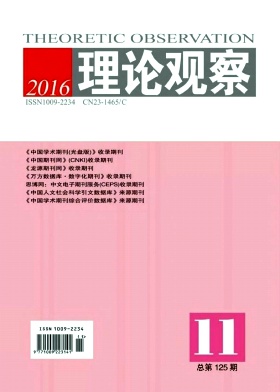法律論文投稿探究清單式法治思維的特點與邏輯基礎(chǔ)
簡要:清單式法治思維力圖避免法律漏洞,用二分法劃分的方式規(guī)定、強調(diào)和突出一個方面,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 法律論文投稿 :探究清單式法治思維特點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清單式法治思維力圖避免法律漏洞,用二分法劃分的方式規(guī)定、強調(diào)和突出一個方面,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法律論文投稿:探究清單式法治思維特點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法治給予了共和國民眾莫大的希望與力量,給予法學(律)人無限的激情與才思。轉(zhuǎn)眼間,新千年又過去15年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quán)威也在于實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關(guān)鍵在于提升法律的實施力和權(quán)威性。然而,當代中國社會正處于急劇轉(zhuǎn)型期(體制轉(zhuǎn)型期與融入WTO過渡期),正處于“三大跨越”(農(nóng)業(yè)社會向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向信息社會)同時并舉的歷史階段。這樣一個時期,社會立法肯定會總體落后于社會轉(zhuǎn)型,法律會面臨不少“空白地帶”.面對這些不可避免的空白地帶,清單式法治思維是保證法律實施的一種有效途徑。那么,什么是清單式法治思維?清單式法治思維的特點和邏輯基礎(chǔ)是什么呢?
一、什么是清單式法治思維?
近兩年來,無論是國內(nèi)還是世界范圍,無論是改革還是外交,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權(quán)力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成為一個熱點、一種法治思維模式,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和突破口。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實行統(tǒng)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chǔ)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lǐng)域。”有關(guān)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guī)則段落中明確指出:“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決定》第十部分“強化權(quán)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第35條提出“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quán)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quán)力運行流程”.①由于法治的原初含義和核心價值即限制公權(quán)力和保護私權(quán)利,近代人類社會法制的基本架構(gòu)中,公法私法之分明確了政府享有權(quán)力的領(lǐng)域與政府交給市民社會的領(lǐng)域。有學者認為,限制政府權(quán)力的最好做法是制定“權(quán)力清單”,權(quán)力清單向社會公開,政府只能行使清單中列舉的權(quán)力,清單之外政府無權(quán)行使任何權(quán)力。保障公民權(quán)利的最好做法是制定“負面清單”,“負面清單”也向社會公開,清單列舉禁止公民從事的項目,凡清單未禁止者都是公民權(quán)利的范圍[1].這樣,法治首先明確了公共領(lǐng)域之治和私人領(lǐng)域之治的區(qū)別。在公法領(lǐng)域,奉行“權(quán)力法定原則”,“法未授權(quán)不可為”.法治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行事,“法無授權(quán)不可為”成為中共治國理政的“底線思維”.在私法領(lǐng)域,奉行“私法自治原則”,私法自治原則意味著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私法主體自由意志的干預。換句話說,只要行為人不實施侵犯他人合法的私人領(lǐng)域這一為法所禁止的不正義行為,他就享有充分的自由。“法不禁止皆自由”力圖宣示,扣除禁令后剩余的所有空間均為自由的領(lǐng)地,由此凸顯了自由為“扣減權(quán)”的無所不包的特性,從而營造了最大的自治空間[2].法律是一個規(guī)范體系,來自“應該是”的范疇。
規(guī)范不是對存在著的關(guān)系的簡單確認,規(guī)范之所以是規(guī)范(能夠稱為規(guī)范)主要在于規(guī)定一定數(shù)量的義務和權(quán)限,這些義務和權(quán)限即便是在主體違反或不使用的時候仍然是有效的。信息時代尤其需要底線思維,法律是行為的底線。“負面清單”
制度盡可能擴大市場主體的權(quán)利范圍,明確法律禁止的行為,除了法律禁止的行為都是可以嘗試創(chuàng)新的領(lǐng)域,公權(quán)力不能干涉。“權(quán)力清單”制度,規(guī)范和明確權(quán)力運行的程序、責任,使之可執(zhí)行、可考核、可問責。這就意味著將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以制度規(guī)范權(quán)力,讓權(quán)力運行的邊界公之于眾。
這種運用“權(quán)力清單”“負面清單”或“正面清單”②實現(xiàn)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模式,可以稱之為清單式法治思維。“耶林對法律的科學性所進行的追問,從他提出的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今天都還沒喪失其現(xiàn)實性。”[3]轉(zhuǎn)型時期國家立法頻繁,法律變遷速度加快,對法律科學性的追問變得更為迫切。運用清單式法治思維立法具有什么特點,這種立法(準立法)模式是否科學呢?
二、清單式法治思維的特點
清單式法治思維具有簡單、確定、易判斷的特點。
1.簡單
轉(zhuǎn)型社會最大的特點是社會事務復雜、多元。
劃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復雜問題簡單化,劃分也是解決任何復雜問題的萬能鑰匙。二分法劃分是劃分中最簡單、不可能違背任何邏輯規(guī)則的一種劃分方法。這種方法的步驟是:把A劃分為B和非B兩個互為矛盾關(guān)系的概念或命題。這樣,A中的任何一個分子,不屬于(是)B則肯定屬于(是)非B,不屬于(是)非B則肯定屬于(是)B.權(quán)力清單采取“職權(quán)法定”原則,法未授權(quán)不可為;負面清單采取“非禁即入”模式,法無禁止即自由。
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都采用列舉的方法規(guī)定,都是運用二分法劃分方式立法(包括準立法).在邏輯形式上二者并無區(qū)別,但是質(zhì)量優(yōu)劣可以辨別。例如,國外商業(yè)銀行的業(yè)務,在法律上通常只規(guī)定什么業(yè)務不能經(jīng)營而不規(guī)定什么業(yè)務可以經(jīng)營,以負面清單的方式規(guī)范商業(yè)銀行業(yè)務。我國正好反過來,我國《商業(yè)銀行法》第3條列舉了14類可以經(jīng)營的業(yè)務,也就是說,我國法律以正面清單的方式規(guī)定什么可以經(jīng)營,不規(guī)定什么不能經(jīng)營[5].“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兩種不同的規(guī)定方法,體現(xiàn)出兩種不同的監(jiān)管思路:前者的思路是凡是法律沒有規(guī)定禁止的就都是可以經(jīng)營的;后者的思路是凡是法律沒有規(guī)定可以經(jīng)營的就都是不可以經(jīng)營的。判別哪一種規(guī)定方法更科學的形式標準是看哪一種規(guī)定更簡單。“一個法律系統(tǒng)包含的規(guī)則愈多,一些或者許多規(guī)則不被遵守的風險愈高。這就是發(fā)達福利國家的悖論:規(guī)則愈多,全部或大部分相關(guān)人士知道它們的可能性愈小,規(guī)則之間相互沖突、帶來解釋難題和或被迫地忽視某一規(guī)則的風險愈高,控制并有效制裁不被期待行為的困難和代價也愈大。所有這一切一般性地削弱了法律的權(quán)威性,使實施規(guī)則和指引人的行為變得更為困難,甚至在更為根本的問題上。”
由此看出,包含規(guī)則較少,盡量簡單的法律系統(tǒng)更科學,更便于人們遵守。此外,判別哪一種規(guī)定方法更科學的實質(zhì)標準是哪一種規(guī)定讓市場主體權(quán)利空間更大。在實踐中,人們通常認為,列舉負面清單的方法可以賦予市場主體更大的自治空間和更多的權(quán)利。
2.確定
有學者考察,將法律界定為要求、禁止或者允許并沒有什么新意,因為12世紀的教會法學家已經(jīng)做到了這一點。①馬西利烏斯首先指出,“要求”一詞指的是肯定性的法規(guī)(相當于法律規(guī)范中的“應當”或“必須”),否定性的法規(guī)有自己的特別名稱“禁止”.“不過,要求性的和禁止性的法規(guī)并不能涵蓋法規(guī)的全部,因為有一部分法規(guī)在人們實施或者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時候并不對其施以懲罰,例如慷慨的行為。這種法規(guī)就是‘允許性的'.”[6]允許性法規(guī)在法律中怎樣表述呢?馬西利烏斯還進一步指出:“因為這種允許性法規(guī)的數(shù)量太大了,因此只要有一個一般性的法規(guī)就足夠了。因為任何事情只要是不被法律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就應該被理解為是被允許的。因此允許性的LEX就是不使任何人受到懲罰的立法者的命令,它不強迫或禁止任何人的行為,它只是限定一個人合法地根據(jù)自己的意志進行自由選擇的范圍。”[6]
我國著名民法學家王利明教授認為,作為一種市場準入管理模式,負面清單充分體現(xiàn)了私法自治精神,是私法自治精神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減少市場主體所面臨的新業(yè)態(tài)準入風險、降低市場主體的創(chuàng)新風險、化解市場主體在法律空白領(lǐng)域的風險及減少法律行為效力的不確定性[7].我認為,關(guān)鍵不在于正面清單還是負面清單,而在于立法的時候,理智的立法者能夠確定的是什么,是關(guān)于允許的規(guī)定,還是關(guān)于禁止的規(guī)定。
3.易判斷
在實踐中,如果法律沒有規(guī)定就等于允許,那么法律對允許的規(guī)定就是多余的;如果法律沒有規(guī)定就等于禁止,那么法律對禁止的規(guī)定也是多余的。所以,可以說“法無規(guī)定即禁止”,如果法律只對它允許的行為做出規(guī)定;也可以說“法無規(guī)定即允許”,如果法律只對它禁止的行為做出規(guī)定。
換句話說,如果法律只規(guī)定了哪些是禁止的,那么沒有禁止即等于允許;如果法律只規(guī)定了哪些是允許的,那么沒有允許即等于禁止。比如,對于關(guān)系民生的
食品安全問題,法律可以只規(guī)定禁止添加的東西,沒有禁止的都能添加;也可以只規(guī)定允許添加的東西,沒有允許的東西都不能添加。前者“法不禁止即允許”,后者“法不允許即禁止”.兩者邏輯含義一樣,但是價值上的意義不一樣。
前者側(cè)重于給食品生產(chǎn)者更多自由,因而只有科學表明對人體有較大危害的東西才會規(guī)定不能添加,鼓勵創(chuàng)新,同時也意味著消費者承擔更多的判斷與安全識別風險。后者給予生產(chǎn)者更多限制,只要沒有科學證據(jù)表明對人體無危害的都不能添加,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不需要承擔太多的安全識別風險。
以上這些特點保證了清單式法治思維的邏輯性,保證了權(quán)力清單制度和負面清單制度的科學性。如果不具備這些特點,就不是科學的清單式法治思維。
三、清單式法治思維的邏輯基礎(chǔ)
清單式法治思維的邏輯基礎(chǔ)是:法律沒有規(guī)定不能必然地推出法律允許。②當法律對一種行為p及其相反行為非p都沒有規(guī)定時,我們才可以說法律對于這種行為沒有規(guī)定。假設(shè)p指某種行為,在邏輯關(guān)系上,允許p和允許非p不能同假卻可以同真,對一種行為是允許的,對其相反行為可以是允許的,也可以是不允許的---允許p推不出允許非p;同時,禁止p和禁止非p不能同真卻可以同假,任何時候都不能既禁止p,又禁止非p,這是不證自明的[8].“’不禁止p‘等于’允許p‘”不能證明“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許的”.因為,“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許的”涉及的是全部行為(p和非p),而“’不禁止p‘等于’允許p‘”只涉及部分行為(p),非p中存在法律沒有規(guī)定的行為,這部分行為不可能是法律禁止的,但也不能邏輯地推出就是法律允許的。以下是其證明:“法律沒有規(guī)定”意味著法律對一種行為p及其相反行為非p都沒有規(guī)定。(歸謬法)假設(shè)從法律沒有規(guī)定(p和非p)推出“法律禁止(p和非p)”,則一定會出現(xiàn)邏輯矛盾。因為禁止p和禁止非p不能同真,我們不能既禁止闖紅燈又禁止不闖紅燈。
這個推理可以表示為:((A→B)∧~B)→~A,所以,假設(shè)不成立;假設(shè)從法律沒有規(guī)定p和非p推出“法律允許(p和非p)”則不會出現(xiàn)邏輯矛盾。因為允許p和允許非p可以同真。但是盡管沒有矛盾,((A→B)∧B)→A卻不是必然的推理。也就是說,僅僅根據(jù)“法律沒有規(guī)定推不出法律禁止”,不能證明法律沒有規(guī)定就等于法律允許,除非法律禁止的和法律允許的是矛盾關(guān)系,非此即彼[8].然而,大量存在“法律沒有規(guī)定”的本身,就說明了法律禁止的和法律允許的不是矛盾關(guān)系而是反對關(guān)系[8].在這種情況下,即當存在法律空白的時候,法律沒有規(guī)定不能必然地推出法律允許。也就是說,“法無禁止即自由”這個命題在法律空缺存在的時候,在人們執(zhí)行法律的意思達不到百分之百的時候,不能必然成立。
假如法律規(guī)定了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允許的,二者都沒有窮盡,①此時如果沒有“法律沒有規(guī)定即允許”或者“法律沒有允許即禁止”這個一般性兜底條款,那么法律體系肯定存在漏洞。“當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且又沒有一普遍原則可以適用的情況稱為法律漏洞。奉行’不是法律禁止的即是法律允許的‘原則的法律體系就是排除了所有的法律漏洞的,在這個意義上規(guī)范是完善的。”[9]136沒有漏洞的法律體系是完美的。目前我國很多地方政務改革中提出“一個中心對外、一個窗口受理、一條龍服務、一站式辦結(jié)”,正是避免了服務盲區(qū),方便了群眾。
綜上,清單式法治思維力圖避免法律漏洞,用二分法劃分的方式規(guī)定、強調(diào)和突出一個方面(禁止的或者允許的行為),再使用一個兜底命題(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允許的,或者法律沒有授權(quán)即不可為),以此來清晰界定法律沒有禁止(或授權(quán))的空白地帶(或稱為法律的沉默空間、法律漏洞、法律空缺).法律是一個規(guī)范體系,來自“應該是”的范疇。因此,規(guī)范不是對存在著的關(guān)系的簡單確認,規(guī)范之所以是規(guī)范(能夠稱為規(guī)范)主要在于規(guī)定一定數(shù)量的義務和權(quán)限,這些義務和權(quán)限即便是在主體違反或不使用的時候仍然是有效的。清單式法治思維的立法邏輯,明確了行為的界限,避免了規(guī)范的盲區(qū),擴大了法律調(diào)整的范圍,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深淺。人民日報感言:培育法治文化涵養(yǎng)法治精神[N].人民日報,2014-10-13(6).
[2]易軍。“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私法精義[J].中國社會科學,2014(4):121-142.
[3]魯?shù)婪?middot;馮·耶林。法律是一門科學嗎?[M].李君韜,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4]馬克·范·胡克。法律的溝通之維[M].孫國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7.
[5]龔柏華。“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理與上海自貿(mào)區(qū)“負面清單”模式[J].東方法學,2013(6):137-141.
[6]方新軍。權(quán)利概念的歷史[J].法學研究,2007(4):80.69-95.
[7]王利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與私法自治[J].中國法學,2014(5):26-40.
[8]張靜煥。法律邏輯視域中的“禁止”和“允許”[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6):62-67.
[9]伊爾瑪·塔麥洛。現(xiàn)代邏輯在法律中的應用[M].李振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136.
投稿期刊推薦:
《理論觀察》雜志是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主辦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shù)理論期刊,雙月刊,雙月出版,國際流行大16開本,每期11印張,176頁。本刊已有20年的辦刊歷史。她的前身是《齊齊哈爾社會科學》,于1985年2月創(chuàng)刊,1993年經(jīng)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為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的哲學社會學綜合性學術(shù)理論期刊;后經(jīng)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于2000年2月更名為《理論觀察》。經(jīng)過20年的發(fā)展,《理論觀察》雜志業(yè)已成為在全國社科期刊界小有影響的地方主辦的學術(shù)理論期刊,她的作者遍及全國各地,每期都有多篇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心全文轉(zhuǎn)載、介紹,亦有文章被《新華文摘》刊用或摘編。進入新世紀以來,《理論觀察》已成為各地高等院校博士生、碩士生發(fā)表學術(shù)成果的重要陣地,大批精英人士的加盟和精品之作的惠顧,為《理論觀察》雜志的發(fā)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并鞭策她不斷向新的更高的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