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tǒng)意義上的學習空間主要是指用于學習的場所。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是指基于人工智能技術(shù)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調(diào)動學生活動參與的自主性、促成師生之間以及生生之間的交互行為、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達成學生的深度學習的學習場所。當前,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還存在著設(shè)計觀念陳舊、交互弱化以及人機關(guān)系異化等諸多問題。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構(gòu)建問題的應(yīng)對需要及時更新教師的空間觀念,推進學習空間的發(fā)展;需要深化人工智能技術(shù)研究,構(gòu)建交互型的學習空間;需要正確審視人工智能,防止學習空間的人機關(guān)系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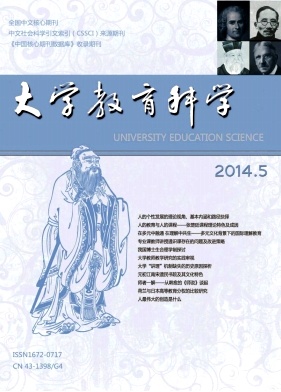
本文源自大學教育科學,2020(05):89-95.《大學教育科學》是經(jīng)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新出版(2002)936號]文件批準,由原1984年創(chuàng)刊的《機械工業(yè)高教研究》更名的高等教育類學術(shù)研究期刊,現(xiàn)已成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索引目錄(CSSCI)來源期刊(2014-2015年),也是《中國學術(shù)期刊(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wǎng)》的期刊源,曾榮獲首屆《CAJ-CD規(guī)范》執(zhí)行優(yōu)秀期刊獎。她還是《中國核心期刊數(shù)據(jù)庫》收錄期刊,在"萬方數(shù)據(jù)—數(shù)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網(wǎng)。《大學教育科學》堅持理論探討與應(yīng)用研究相結(jié)合,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服務(wù),為教育科學的繁榮服務(wù)。
學習空間的研究起源于教學空間。20世紀90年代之前,學習空間與教學空間的概念是互用的。2006年,美國學者戴安娜·奧布林格主編的《學習空間》一書指出了學習空間面臨的技術(shù)挑戰(zhàn)及其空間設(shè)計的發(fā)展趨勢[1],關(guān)于學習空間的理論研究由此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在實踐中,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也成為當下教育領(lǐng)域研究的熱點問題。例如,國內(nèi)外目前主要存在5個典型的大學學習空間的研究項目,分別是我國的未來課堂項目,美國的TEAL項目、SCALE-UP項目、TILE項目,以及澳大利亞的改造大學學習空間項目[2](P82-94)。這些實踐項目為人們理解學習空間的內(nèi)涵提供了良好的例證依據(jù)。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利用數(shù)字計算機或者數(shù)字計算機控制的機器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感知環(huán)境、獲取知識并使用知識獲得最佳結(jié)果的全新系統(tǒng)[3],通常包括機器學習、知識圖譜、人機交互、虛擬現(xiàn)實/增強現(xiàn)實等關(guān)鍵技術(shù)。人工智能為學習空間的發(fā)展提供多種可能性,也給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帶來諸多挑戰(zhàn)。那么,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究竟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正確地審視與思考這些問題成為了當下教育教學領(lǐng)域中的關(guān)鍵議題。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內(nèi)涵
學習空間是指服務(wù)于學生學習的場所。它可以分為真實的物理學習空間與虛擬的物理學習空間兩類[2](P82-94)。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可以被看作是基于人工智能技術(shù)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調(diào)動學生活動參與的自主性、促成師生之間與生生之間的交互行為、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達成學生的深度學習的學習場所[4]。其目的旨在滿足教學形態(tài)的新需求,落實高階思維、社會交互等素養(yǎng)的學習目標[5]。學習空間的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其一,智能性。人工智能可以為學生提供智能學習環(huán)境,實現(xiàn)智能推送學習資源、智能監(jiān)督學習進度以及智能輔導(dǎo)學習問題等功能。人工智能也可以為學生學習營造溫馨安逸的氣氛,它能夠智能調(diào)試學習空間的溫度、濕度與照明度,也能夠智能調(diào)節(jié)桌椅設(shè)備的高度、顏色等。例如,華東師范大學啟動的未來課堂項目能夠通過調(diào)控學習空間的各項系數(shù)以改善師生的體驗感。其二,交互性。人工智能可以保障學習空間內(nèi)交互路徑的暢通性,支持師生之間、生生之間以及教學主體與教學內(nèi)容之間的多主體與多方向交互,使得每個人既是交互的主體,也是交互的客體,增強了學習空間交互的智能性[6]。例如,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發(fā)起的SCALE-UP項目,主張構(gòu)建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互動式的學習空間,利用體驗式、探究式的學習方法,鼓勵學生主動探討問題、分享觀點,改善學習空間內(nèi)的交互效果。其三,協(xié)同性。人工智能作為教學助手,可以幫助教師解決單一重復(fù)的教學問題,助力教師投入時間、集中精力培養(yǎng)學生的高階思維,與教師共同實現(xiàn)高效化的教學。同時,人工智能還可以作為學習伙伴,與學生在協(xié)同學習的場景中共同完成協(xié)同作業(yè)、社會交互等學習任務(wù)。例如,澳大利亞教學委員會開展的改造大學學習空間項目,強調(diào)改造傳統(tǒng)學習空間,支持同伴教學與協(xié)作學習。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價值意蘊
首先,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可以調(diào)動學生學習的能動性。人工智能技術(shù)可以依據(jù)學生的學習風格等基本信息,為學生設(shè)計個性化的學習方案,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密切關(guān)注學生的學習進展情況,靈活調(diào)整其學習步驟,給予學生針對性的教學指導(dǎo),滿足學生學習的個性化需求,提升其學習能動性。同時,人工智能技術(shù)也可以使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更加人性化,幫助教師充分考慮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情況,增強學生學習的自信心,樹立學習主體性意識,助推學習空間內(nèi)每一位學生的主體性發(fā)展。此外,人工智能技術(shù)還可以對學生心理進行測量,研究其內(nèi)隱的心理活動,精準聚焦其個性化的學習路徑,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促使學生積極參與學習空間中的每一項學習活動。
其次,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能夠有效增強學生進行知識學習的情境體驗感。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智能技術(shù)可以創(chuàng)設(shè)“沉浸式”的學習情境,將傳統(tǒng)學習空間中學生由于其想象力的局限性而無法直接感受到的教育內(nèi)容以三維立體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于是,學生就會“設(shè)身處地”思考問題,而不是處于一種“置身事外”的狀態(tài),其潛在的求知欲就會被激發(fā)出來。此外,人工智能技術(shù)還可以利用3D模型增強學生對學習空間的情境認知感[7];同時,它也可以利用虛擬空間幫助學生獲得情境存在感,讓學生專注于學習情境當中。這樣,學生就可以真實感知知識的生產(chǎn)過程以及理解知識的附加價值,進一步豐富自身知識學習的情境性意義和社會價值。
再次,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有利于發(fā)展學生的高階思維。人工智能技術(shù)以專家系統(tǒng)和深層學習方法為主線,變平面化、枯燥化的知識信息為圖形、動畫等生動形象的內(nèi)容,有助于學生理解知識點的性質(zhì),明晰知識點之間的關(guān)系,梳理知識加工過程的邏輯層次,鍛煉學生的邏輯思維。同時,人工智能技術(shù)可以為學生提供直觀體驗與交互體驗的方式,幫助學生突破其想象力的界限[8]。于是,學生對于知識的認識可以擺脫片面性,形塑自身的整體性思維。此外,教師還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為學生設(shè)定多元化的分析視角,啟發(fā)學生站在問題的對立面進行思考,促使學生學會辯證看待問題,激發(fā)學生的批判意識,發(fā)展學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構(gòu)建的問題
(一)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觀念陳舊
人工智能為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空間設(shè)計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然而,在當前實際情況中,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依然沒有掙脫斷裂式的時空觀與片面的空間載體觀的束縛。
首先,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仍然沒有拋棄斷裂式的時空觀念。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應(yīng)當不但可以發(fā)生在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種時態(tài)下,還需要具備由長、寬、高所組成的三維立體構(gòu)型。然而,在實際的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過程中,人們?nèi)耘f秉承傳統(tǒng)的斷裂式的時空觀。學習空間僅僅存在于當時、當下,局限在片段式、橫截面狀、孤立的場域之中,具有割裂式、間斷性的缺點。例如,教師在學習空間中的課前導(dǎo)入籠統(tǒng)、單一且浮于形式,沒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把握每一位學生的已有的認知基礎(chǔ)與一貫的認知風格,難以滿足學生學習新知的個性化需求。這會導(dǎo)致學生新舊經(jīng)驗之間缺少“溝通的橋梁”,學生的學習顧此失彼,出現(xiàn)鋪墊上面的缺口,前后銜接不足,缺乏整體性、連貫性與系統(tǒng)性。于是,這也造成了過去、當下與未來的學習空間之間失去密切的聯(lián)系,學生尚不能隨時隨地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內(nèi)開展一系列的學習活動。雖然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穩(wěn)步向前發(fā)展,但是,這種陳舊的時空觀念將會導(dǎo)致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在具體構(gòu)建層面上的倒退。
其次,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片面強調(diào)知識主導(dǎo)的空間載體觀。當下,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依然以知識為空間的載體,缺少與知識相匹配的教學事件的設(shè)計與情境的構(gòu)建。在這種空間里,知識是學習空間的主宰。學生的學習僅僅停留在知識記憶的淺顯層面,學生對于知識點的來源與用途的理解并不到位,難以自覺探索知識背后蘊含的符號意義。這種片面式的空間設(shè)計觀念就會造成學習空間淪為單一的知識空間,導(dǎo)致學習空間的社會屬性與精神屬性未被真正開發(fā)并處于封閉狀態(tài)。同時,這種學習空間設(shè)計觀念還會導(dǎo)致灌輸式教學的問題,使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異化為用于高效接收知識的場所。眾所周知,每一位學生都存在一個內(nèi)在的自我[9]。教師應(yīng)該利用人工智能,在幫助學生加深對事件的理解與情境的體驗的過程中,喚醒學生自身的生命力,激發(fā)學生多樣化的內(nèi)在知識,啟發(fā)學生個性化的內(nèi)在自我。但是,這種空間設(shè)計理念將會視由外向內(nèi)的知識傳遞為空間的主要活動,忽視學生已有知識的由內(nèi)向外的引導(dǎo),反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加速知識導(dǎo)入的數(shù)量與速度,造成僵化的知識導(dǎo)入式的學習空間。這將會削弱學生的認知能力,抑制學生的問題探索能力,使學生被迫淪為知識灌輸?shù)娜萜?或成為教學生產(chǎn)線上的同質(zhì)性產(chǎn)品,難以滿足每一位學生的個性化的學習需求。
(二)學習空間的交互弱化
交互是空間構(gòu)建的重要因素,它有利于建立學生的知識體系,激發(fā)學生的批判意識以及發(fā)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應(yīng)該存在于教師、學生與人工智能之間所需構(gòu)成的和諧交互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之中。但事實上,教學主體與人工智能在學習空間內(nèi)并未實現(xiàn)多向的深層交互,還存在著線性的單向交互方式與情感交互不足等交互弱化的狀況。
首先,線性的交互方式加劇了學習空間的交互不足。在實際情況中,教師、學生與人工智能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被割裂開來,網(wǎng)狀結(jié)構(gòu)遭受嚴重的破壞,淪為線性的、單向的信息傳遞形式。而且,人工智能自身的線性設(shè)計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習空間的單向交互。人工智能是一種以數(shù)學邏輯為基礎(chǔ)的、計算性的機器創(chuàng)作,它與教學主體之間的交互往往表現(xiàn)為程式化的互動。同時,人工智能具有單向的“思維”方式,即主體輸入知識,智能系統(tǒng)輸出知識[10]。因此,人工智能只是單純對人(教師、學生)發(fā)出的“刺激”作出“反應(yīng)”。這種單向思維導(dǎo)致人工智能在學習空間內(nèi)由教學體驗情境的提供者、學生思維的開拓者淪為機械的答題者,造成教學主體與人工智能之間的交互虛無,體驗式學習的效果不佳,學生思維能力的發(fā)展停滯不前等問題。此外,這種線性的交互方式還會導(dǎo)致學生對學習失去好奇心,對人機交互失去耐心,使學生愈加不適應(yīng)學習空間中的交互活動。學生變得只關(guān)注自身的需求與利益,忽視了集一切教學因素于一體的學習空間的整體性。學生只顧一味地索取而不知回饋,他們愈加排斥學習空間的社會屬性,逃避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人機互動,拒絕加入集體活動。表面上,學生在學習空間內(nèi)進行著“學習”這一社會活動。實質(zhì)上,學生出于極度的自我保護的心理,將自己封鎖在“安全地帶”,置身孤島之中,表現(xiàn)出“離群索居”“自我中心”的孤僻狀態(tài),成為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內(nèi)部的“隱形人”與“非參與者”。
其次,情感交互不足也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交互弱化的重要表現(xiàn)。情感可以對學生的學習發(fā)揮重要作用,情感交互也是人機交互的一項關(guān)鍵內(nèi)容。然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中,人機之間的情感交互并不充分。第一,人工智能獲取情感信息的渠道單一,情感識別不準確。情感是一個由眾多復(fù)雜因素構(gòu)成的綜合性概念,學生情感具有細節(jié)繁多、內(nèi)涵復(fù)雜的特性。同時,情感計算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人工智能對于學生情感特性的認知欠缺周密的考慮,尚未摸索出高水平的人機情感交互的機制。當前,人工智能主要通過識別學生的面部情緒獲取關(guān)鍵的情感信息,情感交互止步于學生情緒的表達。即人工智能可以識別學生做出情感性反應(yīng)的較為明顯的變化過程,卻不能檢測出情感性反應(yīng)的具體內(nèi)容。例如,學生已經(jīng)深刻理解“感人事跡”所傳達的深厚情感,但并未做出強烈的情緒反應(yīng)。這便超出了人工智能進行情緒識別的研究范圍,導(dǎo)致情感計算的結(jié)果失真,造成人機之間缺失了非可操作性情感信息的交互,容易錯失重要的情感細節(jié)。而且,人工智能現(xiàn)有的情感(情緒)數(shù)據(jù)庫尚不完善,與人類本身的情感系統(tǒng)之間存在明顯的排異反應(yīng)。例如,面部識別研究領(lǐng)域所針對的基本情緒(喜怒哀懼等)并不是學習空間內(nèi)高發(fā)的情緒類別(厭倦、疑惑、挫敗等)[11]。第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師對學生的情感認知只是停留在淺表化層面。一方面,教師時常忽視學生情緒的變化,更加關(guān)注學習空間內(nèi)學生數(shù)據(jù)的變化趨勢,僅僅依賴于人工智能對于學生的知識與能力等文本數(shù)據(jù)的分析,難以深入剖析至情感因素,卻提高了人機之間非情感信息的交互速度。另一方面,教師也會忙于處理人工智能提供的各種信息,難以顧及與全體學生的互動交流,難以察覺每位學生透過面部表情等途徑所要傳達的情感需求。師生之間往往缺乏充分的面對面情感交流的機會,教師缺少對學生的真實情感的考慮與權(quán)衡,難以發(fā)掘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于是,情感交互的比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中顯得尤為不足。
(三)學習空間的人機關(guān)系異化
人機關(guān)系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構(gòu)建過程中需要正確審視與認真處理的關(guān)鍵問題。當人們過度關(guān)注人工智能技術(shù)帶來的教學效益的提升時,他們就會淡忘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變革的本質(zhì),造成“重量輕質(zhì)”“本末倒置”的后果,還會在人工智能技術(shù)支持下的學習空間中迷失自我,喪失其主體意識。這將導(dǎo)致學習空間中人機關(guān)系的異化。
首先,人工智能對教學主體的控制引發(fā)了學習空間的關(guān)系異化。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賺取師生的信任,摧毀其模仿力、記憶力與想象力,主宰學習空間中知識的生產(chǎn)過程[12],吞噬師生的主體地位,由外而內(nèi)擴大自身的主權(quán)領(lǐng)域,提高其權(quán)威地位,成為學習空間中課堂教學的發(fā)號施令者,操控教學主體的行為活動。同時,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里,師生也在與人工智能互動的過程中讓渡自身的主體性。對于教學主體而言,技術(shù)似乎已經(jīng)具備改天變地的強大力量,教學主體愈加相信學習空間內(nèi)出現(xiàn)的問題都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技術(shù)得到解決[13]。教師與學生開始沉浸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造的各種便利環(huán)境之中,漸漸迷失了自己,逐漸受到人工智能的控制,淪為技術(shù)的奴隸。例如,人工智能基于自動保存的學生的學習資料,生成個性化的學習者數(shù)據(jù)庫。學生無需個人的努力便輕易獲取自身對于某一問題的疑難點、易錯點等關(guān)鍵信息。這會加劇學生對人工智能的依賴感,損害學生的認知與元認知能力,致使學生愈加不珍惜個性化的學習資源。在現(xiàn)實情況中,教學主體被局限在人工智能搭建的包圍圈內(nèi),他們漸漸失去洞察問題的能動性,自我弱化了問題探索與解構(gòu)的意識,自動降低了自身在學習空間中的主體性地位。總之,教學主體與人工智能之間的地位關(guān)系發(fā)生根本性轉(zhuǎn)變。人工智能與教學主體之間在“一進一退”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完成身份上的交換,形成新的主體與客體、控制與依賴的關(guān)系。
其次,人工智能對教學主體的替代加劇了學習空間的關(guān)系異化。人工智能是對人身體的延伸,它可以用于模擬、擴展人的智能,這寓意著智能技術(shù)與人的進一步融合。然而,人工智能技術(shù)自我更新的速度極快,將為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貢獻更大的力量。教學主體為了更好地發(fā)揮人工智能的功能,竭力追隨教學改革的步伐,不得不強迫自己接受技術(shù)更新的趨勢、掌握相關(guān)知識、熟練運用操作技能。這在表面上是教學主體操縱人工智能,但在本質(zhì)上是人工智能替代了教學主體,實現(xiàn)了對教學主體的反噬。在此過程中,人的身體內(nèi)非生物部分所占比例呈穩(wěn)步上升趨勢,而生物部分的比重卻日益降低,并且生物部分的價值逐漸被人忽視,最終呈現(xiàn)虛擬的身體[14]。更加嚴重的是,人類在未來將被以智能算法和大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的高級人工智能取代,失去對世界的統(tǒng)治權(quán)[15]。可見,在學習空間中,人工智能也正在侵蝕教學主體的生命屬性,并且在潛移默化中掠奪教學主體的身體、侵占其生存空間、壓縮其生命時間。而且,當人長期面對智能設(shè)備時,他的孤獨感、憂郁感就會增加,演變?yōu)榭臻g的孤獨者。于是,人將變得空有軀殼,卻喪失了豐富的精神內(nèi)核,面臨著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淪為“非生命體”的風險。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著學習空間中人機關(guān)系的異化。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構(gòu)建的對策
(一)及時更新教師的空間觀念,推進學習空間的發(fā)展
首先,需革新學習空間的時空觀,擴大學習空間的研究范疇。學校需要聘請人工智能與學習空間領(lǐng)域的專家開展專題講座,組織“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構(gòu)建”的相關(guān)研討活動,幫助教師正視人工智能、掌握操作技能以及理解學習空間、轉(zhuǎn)變時空觀念,將三種時態(tài)(過去、現(xiàn)在、未來)與三種維度(長、寬、高)的學習空間從理想帶到現(xiàn)實,促使立體的時空隧道觀在教師的“概念生態(tài)圈”中更為生動。一方面,在時間觀念上,教師應(yīng)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打破時空束縛,幫助學生從現(xiàn)實空間“穿越”時空隧道來到歷史空間或者未來空間。另一方面,在空間觀念上,教師需要彰顯長、寬、高三維立體的空間形象,發(fā)揮這種呈現(xiàn)方式的優(yōu)勢,激勉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同時,“不同于物質(zhì)實體的自然時空,虛擬時空徹底打破了時間的不可逆性和空間的地理局限”[16],時空觀念的更新將進一步擴大學習空間的研究視野,推動學習空間的發(fā)展由實體空間轉(zhuǎn)向虛擬空間。于是,教師不僅要主動接納學習空間變革的現(xiàn)實,還要積極適應(yīng)人工智能技術(shù)支持下的新的空間樣態(tài),同時警惕純粹的虛擬空間將會導(dǎo)致的空間主體深陷虛無、迷失自我的風險。因此,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研究應(yīng)當切忌“一刀切”,避免學習空間走向虛擬空間的極端,充分利用虛擬學習空間的優(yōu)勢,彌補實體學習空間的不足,促成學習空間的虛實融合。
其次,樹立正確的空間載體觀,沖破知識空間的禁錮。教師應(yīng)該發(fā)揮人工智能特有的虛擬現(xiàn)實與增強現(xiàn)實的功能,以知識為學習空間的承載物,創(chuàng)設(shè)與之相匹配的教學事件與學習情境。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fā)起的TEAL項目,其目的旨在擺脫傳統(tǒng)的填鴨式的知識灌輸觀,并且基于建構(gòu)主義學習理論,構(gòu)建技術(shù)支撐的、有吸引力的主動學習情境。在呈現(xiàn)方式上,這種以情境為知識載體的體驗式學習能夠充分考慮學生的已有認知基礎(chǔ),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強、可接受程度高以及易于理解的優(yōu)點,更利于調(diào)動學生的學習興致,幫助學生的身份變被動為主動,助力學生由機械接收知識信息的容器變身于問題的發(fā)現(xiàn)者、知識解構(gòu)的探索者,使學生頭腦內(nèi)部知識加工的過程可以實現(xiàn)外顯化,認知過程能夠?qū)崿F(xiàn)生動化。于是,學生不僅可以對知識的來源留下深刻的印象,還可以對知識進行遷移,靈活解決具體情境中的相關(guān)問題。此外,教師還應(yīng)拓展學習空間的設(shè)計觀念,由單一的知識空間延伸至社會空間與精神空間。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應(yīng)當建構(gòu)社會關(guān)系、維護空間秩序、增強學習體驗,變僵化、刻板的一維空間為靈活、動態(tài)的多維空間[17]。這愈加有助于學生形成自主學習、善于思考、勇于批判以及敢于創(chuàng)新的優(yōu)秀品質(zhì),從而響應(yīng)高等教育高素質(zhì)人才觀的號召,培養(yǎng)新時代所需的高質(zhì)量人才[18]。
(二)深化人工智能技術(shù)研究,構(gòu)建交互型的學習空間
首先,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應(yīng)當發(fā)揮空間學習網(wǎng)絡(luò)的開放性,強化學習空間的交互功能。學習是建立連接與形成網(wǎng)絡(luò)的過程,也是學習者主動創(chuàng)建個體學習網(wǎng)絡(luò)的過程[19]。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應(yīng)當是一個動態(tài)生成的有機體,支持每一位學生學習網(wǎng)絡(luò)的建立,增強學生個體網(wǎng)絡(luò)之間的互動聯(lián)通。同時,人工智能需要進行技術(shù)革新,“探索能增加每個人的學習機會的各種教育網(wǎng)絡(luò),使得人生時時刻刻都可以進行學習、分享及關(guān)懷。”[20]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需結(jié)合教學主體、教學內(nèi)容、教學手段等教學基本要素,構(gòu)建互聯(lián)互通的空間學習網(wǎng)絡(luò),實時收集與處理交互對象的身份(交互發(fā)起者與交互對象)、交互內(nèi)容、交互手段等交互數(shù)據(jù)[21],充分發(fā)揮交互主體的作用,呈現(xiàn)多樣化的交互形式。此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還應(yīng)當秉承包容的準則,創(chuàng)設(shè)與完善開放、聯(lián)通的空間學習網(wǎng)絡(luò)。基于空間學習網(wǎng)絡(luò)的交互型學習空間將有助于維護學習空間內(nèi)集體的共同利益,保障學生的個體利益,打消學生的個人主義傾向,瓦解學生的“孤島式學習”狀態(tài),將其從封閉的學習空間中解放出來,使學生成為空間學習網(wǎng)絡(luò)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樹立與提升學生的集體責任感,激發(fā)學生活動參與的能動性,破除人機交互的隔閡,克服單個人所具有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狹隘性,實現(xiàn)人的全面性、開放性和完善性[22]。
其次,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還應(yīng)當強化情感交互,挖掘交互內(nèi)容的深度。研究者需要繼續(xù)開發(fā)、完善情緒識別軟件的功能,重點研究學習空間中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學生的學習情緒,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術(shù)支持的情緒數(shù)據(jù)庫。人工智能需要及時擴大情感信息收集的渠道,提升其進行情感識別的精準度,避免錯失學習空間內(nèi)每一位學生的情感數(shù)據(jù),提高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中情感交互的均衡性、高效性與準確性。同時,人工智能應(yīng)當實時收集學習空間中的各種數(shù)據(jù),并通過多樣化的渠道,從學生的面部表情、身體姿勢、語言信息中篩選出情感數(shù)據(jù),提取學生的情感特征,鑒別學生的情感變化,從而幫助教師靈活調(diào)整教學策略,給予學生個性化的情感教學指導(dǎo),有針對性地滿足學生的情感需求。此外,教師也應(yīng)當提高自身對學生情感因素的重視程度,積極參與到學習空間中情感交互的活動中去。教師需要發(fā)揮自身在學生情感分析方面的優(yōu)勢,以個人豐富的執(zhí)教經(jīng)驗為支撐,對人工智能提供的反饋信息進行二次剖析,深入了解學生情感變化的根本原因,為學生提供最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于是,師生之間的交互內(nèi)容將不再停留于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學生也會逐漸感受到來自于教師的情感關(guān)懷,并意識到自身處于被關(guān)心、被照顧、被理解、被尊重的狀態(tài)。這有助于建構(gòu)有溫度、有情懷的學習共同體,打破以信息傳遞與反饋為主的空間交互的機械模式,豐富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構(gòu)建的人文關(guān)懷。
(三)正確審視人工智能,防止學習空間的人機關(guān)系異化
首先,強化師生的主體性意識,防范人工智能的入侵。“人是由上帝之手制造的,任何人制造出的機器都無法與其相比,人的內(nèi)部運動也比任何機器都要神奇”[23]。教學主體需要理性認識人與技術(shù)之間的關(guān)系:人具有主體性,技術(shù)的發(fā)展將受制于人的需求。一方面,師生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真正主體。主體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屬性,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學習空間內(nèi),唯有教師和學生才能稱作教學主體[24]。而人工智能只是一種高階的技術(shù)形式,僅僅具備“非人”的屬性,不能成為學習空間中的主體。而且,師生在學習空間中的主體身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人只有通過人,通過同樣受過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25]盡管,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生在學習空間中的行為表現(xiàn)有所增強。但事實上,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shù),它并不具備育人價值,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對學生的學習行為起到了輔助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shù)受制于教學主體及其教育活動。人創(chuàng)造了人工智能,決定了人工智能的產(chǎn)生。人的需求決定著每一項具體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方向,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整體性也依賴于人的社會活動[14]。而且,人工智能只有在人的使用下才能釋放出更多的能量,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呈現(xiàn)更強大的功能。因此,人工智能背景下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應(yīng)當樹立教學主體的危機意識,發(fā)揚其使命感,從而發(fā)掘?qū)W習空間的人文屬性,使之成為約束人工智能的牽制力[26]。這將有效規(guī)避人工智能逃脫人的束縛,防止其造成重大威脅。
其次,教學主體需要正確把握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消解技術(shù)對人的反噬作用。在學習空間中,人工智能應(yīng)當合理發(fā)揮其技術(shù)特性,擺正其空間服務(wù)者的角色定位,以其技術(shù)邏輯配合教學的育人邏輯,服務(wù)于教師的教學工作,啟發(fā)教師的教學智慧;人工智能應(yīng)著眼于滿足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促進學生的個性化發(fā)展以及推動教與學之間的和諧互動。而且,在學習空間內(nèi),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突破也必須秉承“以生為本”的原則,增強學生進行“沉浸式”學習的體驗感,夯實學生認知發(fā)展的基礎(chǔ),激發(fā)其求知欲并及時擴大研究視域,服務(wù)于學習空間的構(gòu)建。同時,教學主體應(yīng)當掙脫人工智能對其的束縛,維系獨立思考的時間,保留價值判斷的空間,弱化自身對人工智能的依賴性,以其理性與道德制約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異化,有效規(guī)避人工智能技術(shù)對教學主體的反噬作用,扭轉(zhuǎn)學習空間的關(guān)系導(dǎo)向。此外,人工智能也不是一項萬能的設(shè)計,教學主體需要明晰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不足之處。相比較學生自主學習的內(nèi)發(fā)性而言,人工智能技術(shù)具有外在引導(dǎo)性。但事實上,解決學生自身學習問題的根本途徑仍需依賴學生能動性意識的覺醒。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學習空間構(gòu)建的出發(fā)點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既然學生作為研究的服務(wù)對象,他們的學習出現(xiàn)了問題,就應(yīng)遵循從問題中來、到問題中去的原則,厘清問題根源所在,并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
參考文獻:
[1]楊俊鋒,黃榮懷,劉斌.國外學習空間研究述評[J].中國電化教育,2013(06):15-20.
[2]許亞鋒,尹晗,張際平.學習空間:概念內(nèi)涵?研究現(xiàn)狀與實踐進展[J].現(xiàn)代遠程教育研究,2015(03).
[3]中國電子技術(shù)標準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2018版)[R/OL].(2018-01-24)[2019-11-06].
[4]許亞鋒,塔衛(wèi)剛,張際平.技術(shù)增強的學習空間的特征與要素分析[J].現(xiàn)代遠距離教育,2015(02):22-31.
[5]許亞鋒,高紅英.面向人工智能時代的學習空間變革研究[J].遠程教育雜志,2018(01):48-60.
[6]周美云.機遇?挑戰(zhàn)與對策:人工智能時代的教學變革[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0(03):110-116.
[7]蔡蘇,王沛文,楊陽,等.增強現(xiàn)實(AR)技術(shù)的教育應(yīng)用綜述[J].遠程教育雜志,2016(05):27-40.
[8]李洪修,田露.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學自由的價值意蘊及其限度[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20(04):49-55.
[9]尚文鵬.融合與斷裂——對美國波士頓“在家教育”學習網(wǎng)絡(luò)的人類學分析[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4):153-159.
[10]李洪修,吳思穎.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學教學思維的審視與回歸[J].高校教育管理,2020(02):29-36.
[11]陳子健,朱曉亮.基于面部表情的學習者情緒自動識別研究——適切性?現(xiàn)狀?現(xiàn)存問題和提升路徑[J].遠程教育雜志,2019(04):64-72.
[12]張務(wù)農(nóng),賈保先.“人”與“非人”——智慧課堂中人的主體性考察[J].電化教育研究,2020(01):122-128.
[13][美]帕克·帕爾默.教學勇氣[M].方彤,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57.
[14]王志偉.后人類主義技術(shù)觀及其形而上學基礎(chǔ)——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9(08):35-41.
[15][以]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357.
[16]張茂鈺.社會時空關(guān)系的后現(xiàn)代審視[J].寧夏社會科學,2019(02):26-32.
[17]李爽,鮑婷婷,王雙.“互聯(lián)網(wǎng)+教育”的學習空間觀:聯(lián)通與融合[J].電化教育研究,2020(02):25-31.
[18]余小波,張歡歡.人工智能時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觀探析[J].大學教育科學,2019(01):75-81.
[19]郭玉娟,陳麗,許玲,等.聯(lián)通主義學習中學習者社會網(wǎng)絡(luò)特征研究[J].中國遠程教育,2020(02):32-39.
[20][美]伊萬·伊利奇.去學校化社會[M].吳康寧,譯.北京: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17:4.
[21]徐亞倩,陳麗.聯(lián)通主義學習中個體網(wǎng)絡(luò)地位與其概念網(wǎng)絡(luò)特征的關(guān)系探究——基于cMOOC第1期課程部分交互內(nèi)容的分析[J].中國遠程教育,2019(10):9-19.
[22]王文東.《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的空間正義思想解讀[J].哲學研究,2016(04):8-14.
[24]程良宏,孟凡麗.生成性教學:作為教學哲學的機理結(jié)構(gòu)與內(nèi)在理據(jù)[J].課程·教材·教法,2016(09):73-79.
[25][德]康德.論教育學[M].趙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
[26]張祥云,柳蔚.為機器立心:智能時代教育的人文使命[J].大學教育科學,2019(04):99-106.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