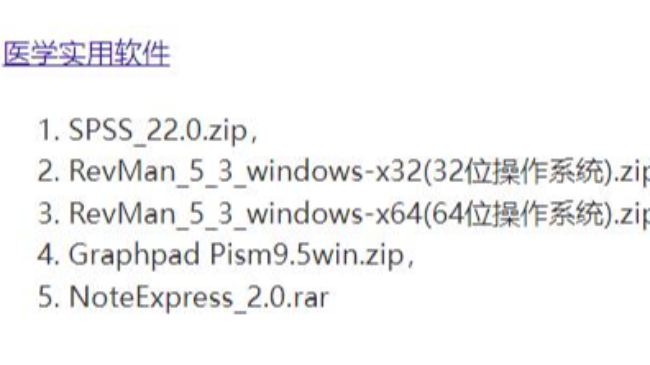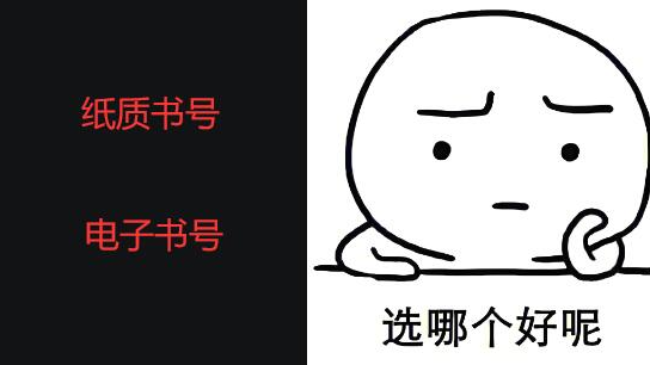拉美后現(xiàn)代文學(xué)傳播與影響
拉美并非后現(xiàn)代的原發(fā)地,但它在后現(xiàn)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卻令世界矚目。拉美的作家在繼承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托馬斯的《魔山》、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審判》等歐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基因的過(guò)程中,沒(méi)有被強(qiáng)大的外來(lái)文化所同化。相反,他們以其頑強(qiáng)的凈化能力,再造了一個(gè)堅(jiān)守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和西班牙混合文化本色的全新的拉美新小說(shuō)體系。他們用自己帶有濃郁加勒比地區(qū)特色的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震撼和影響了世界文學(xué)。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正是從這種最接近自己國(guó)情的后現(xiàn)代思潮的文學(xué)探索中,找到了與當(dāng)今世界文學(xué)流行趨勢(shì)接軌的最佳路徑。
一、拉美后現(xiàn)代文學(xué)
后現(xiàn)代文學(xué)是資本主義后工業(yè)時(shí)期的產(chǎn)物。但是拉美,并沒(méi)有因?yàn)槲闯霈F(xiàn)資本主義工業(yè)生產(chǎn)高度發(fā)展的階段而成為一塊凈土。事實(shí)上,世界文學(xué)在戰(zhàn)后所出現(xiàn)的這股新的后現(xiàn)代文學(xué)思潮,并不妨礙拉美的作家對(duì)世界文化的兼收并蓄。一些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作家在歐美當(dāng)代文學(xué)思潮的影響下,向本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學(xué)發(fā)難。它產(chǎn)生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具有后現(xiàn)代品質(zhì)的作品進(jìn)入人們的視野。就個(gè)人而言,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被推崇為拉美后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標(biāo)志性人物。他的《接近阿爾莫塔辛》被認(rèn)為是20世紀(jì)第一篇后現(xiàn)代小說(shuō),曾引發(fā)了一場(chǎng)小說(shuō)革命,其中所采用的后現(xiàn)代手法,對(duì)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和經(jīng)驗(yàn)主義敘事進(jìn)行了徹底的清算。在傳統(tǒng)與后現(xiàn)代之間,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態(tài)度歷來(lái)是一條重要的分水嶺,博爾赫斯則最具代表性。他對(duì)現(xiàn)實(shí)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懷疑論者的質(zhì)疑態(tài)度,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不可知,充其量是個(gè)象征的系統(tǒng)的理論觀點(diǎn),即使是歐美的作家也難以望其項(xiàng)背。在他的小說(shuō)中,人們只能看見(jiàn)事物表面的神秘面紗,背后的深度模式,往往是望不見(jiàn)底的深淵。他擅長(zhǎng)使用迷宮和時(shí)間的概念,其中,迷宮讓人辨別不清方向,時(shí)間則使現(xiàn)實(shí)撲朔迷離。他的代表作《小徑分叉的花園》將不同的時(shí)間狀態(tài)放在同一個(gè)空間場(chǎng)景中敘述,同時(shí)輔之以迷宮,使故事的敘事顯得云遮霧罩,理不清頭緒。他的創(chuàng)作大都不是直接取材于現(xiàn)實(shí),而是以超強(qiáng)的想象力,從文本的系統(tǒng)中“抄襲”、“拼貼”和“改寫(xiě)”而來(lái)。他的小說(shuō)常用哲人之言,經(jīng)典和歷史事件,以之來(lái)虛構(gòu)出新的故事。他的《阿萊夫》《巴別圖書(shū)館》《特隆•烏克巴爾,奧爾比斯•特蒂烏斯》等小說(shuō),打破現(xiàn)實(shí)與幻想的界限,表現(xiàn)出形而上的世界及現(xiàn)實(shí)行為的虛幻性。就流派而言,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被一些后現(xiàn)代學(xué)者視為典型代表,盡管該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認(rèn)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屬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范疇,但他從卡夫卡、福克納那里學(xué)來(lái)的現(xiàn)代主義表現(xiàn)手法,事實(shí)上對(duì)他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加之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普遍認(rèn)為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發(fā)展到今天,已難以表現(xiàn)拉美的神奇現(xiàn)實(shí)了,它需要借助后現(xiàn)代的手法才能趨于完美。當(dāng)然,也有研究者認(rèn)為,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是拉美的作家用印第安人的眼睛來(lái)看世界。印第安人的愚昧無(wú)知及拉美的神奇現(xiàn)實(shí),往往使觀察的對(duì)象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這些神奇的現(xiàn)實(shí),除去獨(dú)具特色的自然景觀,有關(guān)民間傳說(shuō)、鬼魂故事和印第安人傳統(tǒng)意識(shí)的預(yù)言和預(yù)示部分,其實(shí)正是拉美最具后現(xiàn)代色彩的內(nèi)容。加之拉美傳統(tǒng)的信仰使人堅(jiān)信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有活人與死人的“二元世界”,以及一些人所迷信的吉普賽人的磁鐵、奧雷良諾上校的小金魚(yú)、神父騰空的飛毯等等,都能增添小說(shuō)的后現(xiàn)代效果。胡安•魯爾福是拉美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其代表作《佩德羅•帕拉莫》成功地運(yùn)用后現(xiàn)代的藝術(shù)技巧,將一個(gè)亡靈與現(xiàn)實(shí)的世界結(jié)合在一起,從而在表現(xiàn)印第安部落自由往來(lái)的活人與死人世界的傳統(tǒng)觀念的同時(shí),巧妙地將歐美后現(xiàn)代的藝術(shù)技巧與拉美的現(xiàn)實(shí)融合起來(lái)。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dú)》將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推向了高峰。作家在小說(shuō)中除去對(duì)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反映,在一些故事內(nèi)容的局部和細(xì)節(jié)上,所使用的夸張、變形、荒誕和象征的手法,特別是廣泛借助印第安人傳統(tǒng)的輪回觀念和神話故事來(lái)打破現(xiàn)實(shí)與幻想之間的界限,使之成為最具加勒比地區(qū)特色的后現(xiàn)代巨著。從博爾赫斯、魯爾福、卡彭鐵爾、阿斯圖里亞斯、奧內(nèi)蒂與薩瓦托為代表的拉美先鋒小說(shuō),到以馬爾克斯、科塔薩爾、略薩、福恩斯特與多諾索為代表的“新小說(shuō)”,我們從中都可以看到后現(xiàn)代的蹤影。特別是蘊(yùn)含在這些作家創(chuàng)作中對(duì)總體性和一元性的消解,對(duì)不確定性、偶然性及內(nèi)在性的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理性的“宏大敘事”和“深度模式”的質(zhì)疑等等,紛紛成為中國(guó)作家學(xué)習(xí)和效仿的榜樣。
二、拉美后現(xiàn)代文學(xué)在中國(guó)的傳播
拉美后現(xiàn)代在中國(guó)的傳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三世界國(guó)情上的相似性。封閉、愚昧和落后的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半工業(yè)生產(chǎn)狀態(tài)的社會(huì)原因,拉近了中國(guó)作家與后現(xiàn)代的距離。一方面,人們從拉美作家獲得諾貝爾獎(jiǎng)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對(duì)后現(xiàn)代的好奇與渴望又推動(dòng)了拉美文學(xué)的大量引進(jìn)。
(一)文學(xué)作品的傳播
拉美當(dāng)代文學(xué)在中國(guó)的傳播高潮是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特別是進(jìn)入90年代以來(lái),歐美及俄羅斯經(jīng)典的作家作品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的吸引力日漸減弱,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逐漸轉(zhuǎn)向拉丁美洲,特別是拉美爆炸文學(xué)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作家與作品,普遍公認(rèn)的是富恩特斯、略薩、科塔薩爾和馬爾克斯等人。他們?cè)诙潭淌觊g所寫(xiě)出的作品迅速在中國(guó)走紅,富恩特斯的小說(shuō)《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略薩的《城市與狗》《酒吧長(zhǎng)談》,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馬爾克斯的《周末后的一天》、《枯枝敗葉》和《百年孤獨(dú)》,博爾赫斯的小說(shuō)《小徑分叉的花園》,魯爾福的小說(shuō)《佩德羅•帕拉莫》等是其典型代表,這些作品大都深受中國(guó)讀者的喜愛(ài)。1979年,中國(guó)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xué)研究會(huì)成立,有力地推動(dòng)了拉美文學(xué)在中國(guó)的傳播。中國(guó)社科院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文學(xué)》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的《外國(guó)文藝》雜志,是傳播拉美文學(xué)的重要陣地。1997年,上述研究會(huì)與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拉丁美洲文學(xué)叢書(shū)”,更是把拉美文學(xué)的傳播推向高潮。然而事實(shí)上,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dú)》等小說(shuō),在較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都是以盜版的形式在中國(guó)發(fā)行的,這也從另一個(gè)角度說(shuō)明人們對(duì)拉美文學(xué)的喜愛(ài)。作為拉美后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代表,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還被列入我國(guó)高中教材,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dú)》等小說(shuō)被列為大學(xué)中文課程的必讀內(nèi)容。
(二)創(chuàng)作思想的傳播
就在拉美文學(xué)的名著名篇被引進(jìn)中國(guó)的同時(shí),拉美文學(xué)代表性作家和批評(píng)家的創(chuàng)作思想及理論觀點(diǎn)也開(kāi)始以譯文的形式傳入中國(guó)。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博爾赫斯的論文《討論集》《序言集成》《深沉的玫瑰》《博爾赫斯口述》和《七夕》等;阿根廷南美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路易斯•哈斯的論著《新異端———卡洛斯•富恩特斯》;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1987年出版的馬爾克斯與門(mén)多薩的談話錄《番石榴飄香》,馬爾克斯的《我不是來(lái)演講的》《也談文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海邊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爾克斯《兩百年的孤獨(dú)》等等。盛行于中國(guó)的拉美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的主要理論觀點(diǎn)和創(chuàng)作主張,集中地表現(xiàn)在以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為代表的后現(xiàn)代作家的各類論述中:如前者關(guān)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改寫(xiě)”、“抄襲”、“復(fù)制”和“拼貼”的理論觀點(diǎn);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在已有文本的基礎(chǔ)上,對(duì)原有的材料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使之“煥然一新”;文學(xué)創(chuàng)作“抄出來(lái)的是感覺(jué),是內(nèi)心需要”[1]等等。馬爾克斯關(guān)于“小說(shuō)是用密碼寫(xiě)就的現(xiàn)實(shí),是對(duì)世界的揣度”;[2]文學(xué)作品需要用一種更加豐富多彩的語(yǔ)言,使之進(jìn)入另外一種現(xiàn)實(shí),即那種被人稱之為神話的現(xiàn)實(shí)和魔幻的現(xiàn)實(shí);我要像我外祖母講故事一樣敘述歷史的創(chuàng)作主張等等。卡彭鐵爾關(guān)于拉美的現(xiàn)實(shí)是“神奇的現(xiàn)實(shí)”,神奇的現(xiàn)實(shí)是真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的文學(xué)認(rèn)知等等。拉美作家關(guān)于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認(rèn)識(shí)與理解,以及他們作品中所反映出來(lái)的那種相較于歐美后現(xiàn)代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的前衛(wèi)性、神秘性、超越性和反叛性的文學(xué)藝術(shù)特征,共同構(gòu)成了拉美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思想最核心的內(nèi)容,它們都受到久限于封閉狀態(tài)下的中國(guó)作家的熱烈追捧。(三)理論研究的傳播拉美文學(xué)在中國(guó)的傳播,表現(xiàn)為兩個(gè)深化的過(guò)程:就傳播的內(nèi)容而言,它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從拉美文學(xué)作品的傳播,到創(chuàng)作思想的傳播,再到對(duì)拉美文學(xué)現(xiàn)象的研究傳播的深化過(guò)程;就傳播的重點(diǎn)而言,它又經(jīng)歷了從對(duì)拉美后現(xiàn)代作品的譯介,到對(duì)作品的特征特點(diǎn)分析,再到與歐美后現(xiàn)代的對(duì)比研究、地域特色研究、魔幻寫(xiě)實(shí)研究等更為廣闊和深化的研究領(lǐng)域的過(guò)程。在拉美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研究形式上,既有論著的形式,也有論文的形式。在論著方面,以《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陳光孚著)、《拉美當(dāng)代小說(shuō)流派》(陳眾議著)、《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xué)》(徐玉明著)、《拉美文學(xué)流派的嬗變與趨勢(shì)》《拉美文學(xué)流派與文化》(李德恩著)、《20世紀(jì)拉丁美洲小說(shuō)》(趙德明著)、《加西亞•馬爾克斯研究》(林一安著)、《當(dāng)代拉美文學(xué)研究》(朱景冬著)、《解讀博爾赫斯》(殘雪著)等最具代表性;在論文方面,則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研究資料》(張國(guó)培撰)、《未來(lái)主義、超現(xiàn)實(shí)主義、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柳鳴九撰)、《世界文學(xué)的奇葩———拉丁美洲文學(xué)研究》(中國(guó)西、葡、拉美文學(xué)研究會(huì)編撰)、《當(dāng)代拉丁美洲小說(shuō)與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xué)》(孫家堃撰)等最具影響力。關(guān)于我國(guó)作家和學(xué)者在拉美后現(xiàn)代研究方面的文章數(shù)量,有人做過(guò)粗略統(tǒng)計(jì),從1979到2004年25年間,有關(guān)的研究文章已達(dá)200余篇。其中,理論探討的文章50多篇,其它均為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內(nèi)容,它們分別涉及到馬爾克斯、魯爾福、阿斯圖里亞斯、卡彭鐵爾、彼特里等人。這些研究文章的大量涌現(xiàn),在拉美后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深入傳播方面,無(wú)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拉美后現(xiàn)代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影響
拉美文學(xué)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作家的影響是極為深遠(yuǎn)的。中國(guó)作家朱偉曾說(shuō)過(guò),拉美“這些作品,哺育了一整代80年代的作家,不斷滋養(yǎng)了80年代高潮迭起的文學(xué)革命”。[3]69有人曾作出中國(guó)作家的成長(zhǎng)是吸收了拉美文學(xué)的營(yíng)養(yǎng)的文學(xué)斷言,并非夸大之詞。
(一)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影響
這種思想上的影響,突出地表現(xiàn)為對(duì)拉美創(chuàng)作主張的認(rèn)同與接受。就我國(guó)作家莫言而言,他從馬爾克斯創(chuàng)作中所受到的啟發(fā)是,領(lǐng)悟到作家獨(dú)特的哲學(xué)思想,即認(rèn)識(shí)世界、認(rèn)識(shí)人類的方式,并由此而找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方向。他透過(guò)作家創(chuàng)作形式上的表象,深入理解和把握作家隱藏在內(nèi)心深處關(guān)于世界處于輪回狀態(tài)的認(rèn)知判斷。如在小說(shuō)《生死疲勞》中,他將這種輪回的思想與佛教中的“六道輪回”學(xué)說(shuō)融為一體,從不同的層面講述中國(guó)農(nóng)民與土地的關(guān)系。莫言還從馬爾克斯對(duì)馬孔多鎮(zhèn)和福克納對(duì)約克納帕塔法縣這一單純地域的多元化定位中,認(rèn)識(shí)到地域描寫(xiě)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意義,認(rèn)為這種地域描寫(xiě)正是“立足一點(diǎn),深入核心,然后獲得通向世界的證件”。[3]6受此啟發(fā),莫言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藝術(shù)世界———高密東北鄉(xiāng)。格非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上,從拉美文學(xué)中受到的啟發(fā)和影響,是認(rèn)識(shí)到拉美作家筆下那些被稱為“魔幻”的內(nèi)容,其實(shí)正是作家心目中的真實(shí)現(xiàn)實(shí)。他依照拉美的理論來(lái)認(rèn)識(shí)世界,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性具有時(shí)間和對(duì)象上的差異性,昨天真實(shí)的東西今天可能是神話;作者心目中的現(xiàn)實(shí),讀者可能認(rèn)為是傳奇;歷史或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某些神秘的內(nèi)容甚至?xí)谷藗兊南胂蠡蛱摌?gòu)相形見(jiàn)絀。因此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時(shí)常出現(xiàn)虛幻的故事內(nèi)容,也就不足為奇。博爾赫斯的文學(xué)觀點(diǎn)和在小說(shuō)敘事上的創(chuàng)新,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先鋒作家們的創(chuàng)新實(shí)驗(yàn)亦發(fā)生著深刻的影響。我們從馬原、殘雪、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等人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似乎都能看到拉美文化的痕跡。
(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上的影響
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xiàn)為創(chuàng)作傾向上的相似性和文本中的拉美文化特性。這是一種主動(dòng)性的模仿與借鑒,其成因,主要取決于三個(gè)方面。其一,是中國(guó)作家從拉美后現(xiàn)代的創(chuàng)作中再次發(fā)現(xiàn)藝術(shù)與土地的關(guān)系,特別是那種帶有濃郁家鄉(xiāng)色彩的地區(qū)性描寫(xiě),紛紛成為作家們描寫(xiě)的重點(diǎn)內(nèi)容,如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xiāng)地區(qū)寫(xiě)作,賈平凹筆下的商州地區(qū)創(chuàng)作,閻連科筆下的杷樓山脈地區(qū)創(chuàng)作,鄭萬(wàn)隆筆下的黑龍江地區(qū)寫(xiě)作,李銳筆下的呂梁山地區(qū)寫(xiě)作,馬原、扎西達(dá)娃筆下的雪域高原西藏地區(qū)的寫(xiě)作等等。其二,是讓中國(guó)的作家重新認(rèn)識(shí)到民間資源對(duì)于寫(xiě)作的重要意義。如博爾赫斯在《小徑分叉的花園》中將中國(guó)歷史上的故事與歐洲所發(fā)生的戰(zhàn)事聯(lián)系起來(lái),以增添故事的神秘色彩;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dú)》中加入外祖母講故事般的“幻覺(jué)、預(yù)兆和祈請(qǐng)鬼魂”等事件,以使故事更加符合印第安人觀察事物的獨(dú)特視野。我們從莫言的小說(shuō)中,同樣能夠看到高密歷史上的傳說(shuō)人物和民間故事;從徐小斌的《羽蛇》中,看到太平天國(guó)、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文革中的故事等等。其三,是使中國(guó)作家確立了個(gè)性在寫(xiě)作中的地位,如巴爾加斯•略薩在結(jié)構(gòu)上的努力,卡彭鐵爾在時(shí)間上的創(chuàng)新,馬爾克斯在空間地域上的發(fā)掘,博爾赫斯在文本形式方面的變化等等,均使中國(guó)的作家找到了各自的發(fā)力方向。他們借助拉美后現(xiàn)代“細(xì)雨潤(rùn)物”般的影響,特別是馬爾克斯的魔幻理念,“在之后都有很大的文學(xué)造化”。
(三)創(chuàng)作技巧上的影響
創(chuàng)作技巧上的影響多表現(xiàn)為文本表現(xiàn)手法上的模仿與借鑒。這一現(xiàn)象曾被人稱為“博爾赫斯癥候”、“魯爾福癥候”或“馬爾克斯癥候”。這種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gè)方面。其一,是模仿故事敘事的多維視角。馬爾克斯《百年孤獨(dú)》中的“多年以后……”的后現(xiàn)代句式,成為一種后現(xiàn)代的話語(yǔ)標(biāo)簽,成為那個(gè)時(shí)候中國(guó)作家最為時(shí)髦的小說(shuō)開(kāi)篇。如莫言《紅高粱》中“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蘇童《平靜如水》中“我選擇了這個(gè)有風(fēng)的午后開(kāi)始記錄去年的流水賬……”;陳忠實(shí)《白鹿原》中“白嘉軒后來(lái)最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中……”;周大新《銀飾》中“在那個(gè)薄霧飄繞的春天的早晨……”等等,他們都在竭力使三維的時(shí)空包容更加廣闊的故事內(nèi)涵。其二,是借家族歷史展現(xiàn)社會(huì)歷史畫(huà)卷。中國(guó)的作家在學(xué)習(xí)拉美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的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拉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價(jià)值追求,很大程度上是通過(guò)對(duì)家族的歷史描述來(lái)探尋歷史的根基。于是,我們隨之看到了許多的中國(guó)作家借鑒了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dú)》中以馬孔多和布恩蒂亞家族的歷史來(lái)展現(xiàn)拉美社會(huì)歷史圖景所使用的相似手法,如扎西達(dá)娃在《西藏,隱秘歲月》中以哲拉山區(qū)廓康小村達(dá)朗家族五代人的命運(yùn)來(lái)反映西藏社會(huì)歲月變遷的故事;張煒在《古船》中以隋、趙、李三個(gè)家族的興衰來(lái)反映洼貍鎮(zhèn)從解放前夕到改革開(kāi)放40年間的歷史變遷的故事;蘇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通過(guò)描寫(xiě)家族的陳年往事來(lái)反映作家家族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的生存狀態(tài)的故事等等。其三,是對(duì)家鄉(xiāng)地域的藝術(shù)化表現(xiàn)。如莫言發(fā)現(xiàn)馬爾克斯《百年孤獨(dú)》中的馬孔多、魯爾福《佩德羅•帕拉莫》中的科馬拉村、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中的阿什格羅夫村的那些地方,它們都是作家通向世界的重要“支點(diǎn)”。于是,在中國(guó)作家們筆下,專屬于自己的地區(qū)主義創(chuàng)作成為作家個(gè)人的標(biāo)志性元素,作家們?cè)谡宫F(xiàn)故鄉(xiāng)地域性特征的同時(shí),也書(shū)寫(xiě)進(jìn)了自己最初的生命記憶。其四,是對(duì)迷宮的建構(gòu)。博爾赫斯小說(shuō)中的迷宮現(xiàn)象,一時(shí)成為人們效仿的對(duì)象。他們或是建構(gòu)故事的迷宮,如馬原在《岡底斯誘惑》中玩弄“敘述圈套”,把故事的因果聯(lián)系拆解得七零八碎,然后再用拼接的手法,把一些互不相關(guān)的故事組裝在一起;或是建構(gòu)敘事的迷宮,如格非在《褐色鳥(niǎo)群》中的描述:“淺黃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銳角背部石榴紅色的墻成板塊狀向左向右微斜身體處于舞蹈和僵直之間笨拙而又有彈性地起伏顛簸”,[5]著實(shí)令人費(fèi)解;或是建構(gòu)寓言的迷宮,如王小波用虛構(gòu)的手法突破現(xiàn)實(shí)原則的束縛。他在《紅拂夜奔》中加進(jìn)強(qiáng)烈的寓言性,“煞費(fèi)苦心地把各種隱喻、暗示、映射加進(jìn)去……”,[6]使該小說(shuō)在有趣的同時(shí),更增添了影射的色彩。拉美后現(xiàn)代在中國(guó)的影響是深遠(yuǎn)的。這種影響,不僅僅表現(xiàn)為80年代中后期我國(guó)先鋒創(chuàng)作對(duì)其的模仿與借鑒,還反映在至今仍滲透在中國(guó)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的那種時(shí)而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魔幻或后現(xiàn)代手法。如莫言“將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dāng)代社會(huì)融合在一起”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其實(shí)都是這種影響力還在繼續(xù)發(fā)揮作用的最好證明。
作者:唐希 吳舒妮 單位:成都理工大學(xué) 美國(guó)伊利諾伊理工大學(xué)
本文html鏈接: http://www.cssfps.cn/qkh/614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