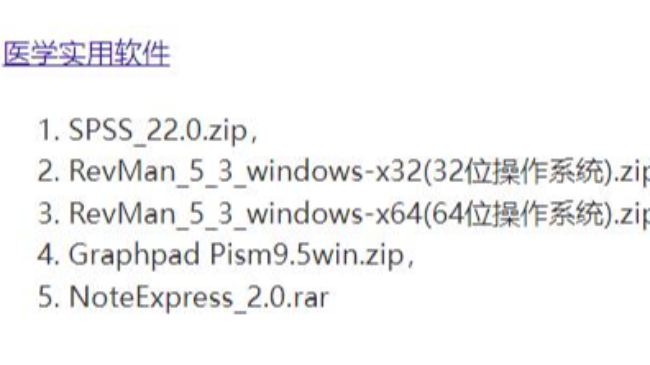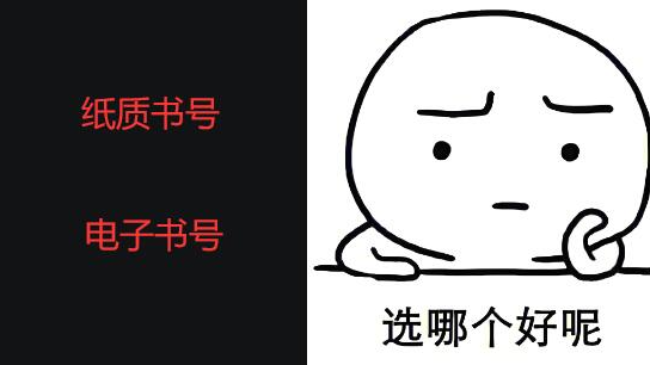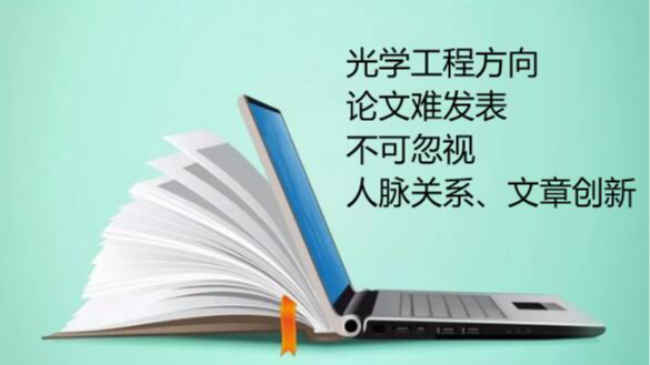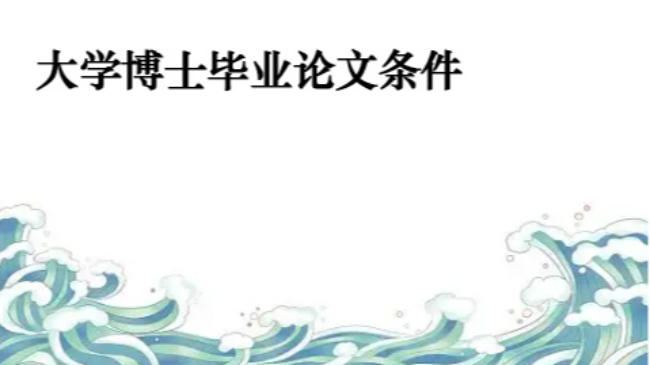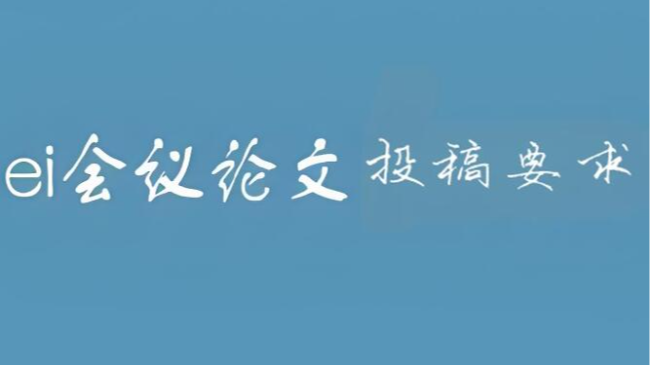中西民族傳統(tǒng)文學(xué)的融合與發(fā)展
一、中西民族傳統(tǒng)文學(xué)對(duì)比
1925年,沈雁冰(本名沈德鴻,筆名茅盾,1896—1981)的第一篇神話研究論文《中國(guó)神話研究》發(fā)表于《小說月報(bào)》第16卷第1號(hào)。他嘗試運(yùn)用歐洲人類學(xué)派的神話理論來闡釋中國(guó)神話問題。他在論述中國(guó)神話之前,先援引了安德魯•蘭(AndrewLang,1844~1912)和麥根西(A.Mackenzie,通譯麥肯齊)的主要觀點(diǎn),作為他論述中國(guó)神話的理論根據(jù),說:“我們根據(jù)了這一點(diǎn)基本觀念,然后來討論中國(guó)神話,便有了一個(gè)范圍,立了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他根據(jù)蘭氏的原則,理出來研究中國(guó)神話的“三層手續(xù)”(即三條原則):第一,區(qū)別哪些是原始神話,哪些是神仙故事。第二,區(qū)別哪些是外來的神話,哪些是本土神話。第三,區(qū)別哪些神話受了佛教的影響。他認(rèn)為,如果按照這三條原則來研究中國(guó)神話資料,則表現(xiàn)中華民族的原始信仰與生活狀況的神話就會(huì)凸現(xiàn)出來。這三條原則,特別是后兩條,實(shí)際上是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神話與外國(guó)神話的比較研究的原則。與朱光潛、梁宗岱一樣有著留洋經(jīng)歷,一樣有著扎實(shí)的國(guó)學(xué)與西學(xué)修養(yǎng)的錢鐘書(1910~1997),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踏入了比較文學(xué)園地。與朱光潛、梁宗岱一樣,他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在中西詩歌領(lǐng)域,但與朱光潛的邏輯化、體系化的研究不同,錢鐘書更傾向于以SU.g隨筆的方式,信手拈來地做中西比較,在這一點(diǎn)上有點(diǎn)近似梁宗岱。但他是個(gè)極重文獻(xiàn)的研究家,對(duì)文獻(xiàn)的引用不厭其煩,這與梁宗岱的徑直爽快的評(píng)論風(fēng)格又形成對(duì)照。這一時(shí)期,錢鐘書除了用中文和英文發(fā)表了幾篇文章,如《中國(guó)固有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一個(gè)特點(diǎn)》(《文學(xué)雜志》1卷4期,1937)之外,在學(xué)術(shù)研究方面的主要作品是以品評(píng)中國(guó)古典詩歌為中心的隨筆札記集《談藝錄》。《談藝錄》寫于1939年至1942年間,1948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全文用文言文寫成,文字較為古奧,其間有夾雜一些英文引文,引述資料顯得堆砌、繁復(fù)、瑣屑,非專業(yè)讀者讀通不易。《談藝錄》有九十一則札記,后又增補(bǔ)十八則“補(bǔ)遺”。以唐代以降的中國(guó)詩為話題,對(duì)詩人、詩派、風(fēng)格、軼聞趣事等加以品評(píng),都是一些片斷性的文字,篇與篇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lián)系,沒有多少術(shù)語概念,沒有理論命題,更沒有體系的構(gòu)建,結(jié)構(gòu)比較松散,內(nèi)容比較駁雜,行文比較自由散漫,這些都使得《談藝錄》頗似中國(guó)傳統(tǒng)的詩話。進(jìn)入現(xiàn)代之后,這種傳統(tǒng)詩話式的寫作與研究方式幾乎無人為之了。但這種寫法似乎很適合錢鐘書那種不趕時(shí)髦不從眾,自由灑脫的學(xué)術(shù)個(gè)性,因而用起來顯得得心應(yīng)手。更重要的,《談藝錄》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話,因?yàn)槠渲袏A雜了大量的外國(guó)文學(xué)、外國(guó)文化的旁證材料,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為傳統(tǒng)詩話所不及。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研究比較文學(xué)的人,有理由把它視為比較文學(xué)的成果。錢鐘書在談?wù)摬艘恢袊?guó)話題的時(shí)候,必以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對(duì)的材料作為佐證或旁證,以強(qiáng)調(diào)他在序中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xué)北學(xué),道術(shù)未裂”的世界文學(xué)整體觀。中西詩歌的比較研究首推朱光潛(1897~1986)。朱光潛在1934年發(fā)表《長(zhǎng)篇詩在中國(guó)何以不發(fā)達(dá)》(原載《申報(bào)月刊》第3卷第2號(hào))一文,試圖解釋中國(guó)的長(zhǎng)篇敘事詩缺乏的原因。這個(gè)問題梁?jiǎn)⒊缭凇讹嫳以娫挕分芯鸵烟崞穑f:“希臘詩人荷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為今日考據(jù)希臘史者獨(dú)一無二之秘本。每篇率萬數(shù)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爾頓、田尼遜等,其詩動(dòng)亦數(shù)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guó)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學(xué)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zhǎng)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為日月爭(zhēng)光,然其精深盤郁雄偉博麗之氣,尚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干七百余字,號(hào)稱古今第一長(zhǎng)篇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于世運(yùn)無影響也。”在這里,梁?jiǎn)⒊^早明確指出了中國(guó)文學(xué)長(zhǎng)篇敘事詩的不發(fā)達(dá),為中西比較文學(xué)提出了一個(gè)研究課題,朱光潛則試圖對(duì)這個(gè)問題做出探討和回答。
二、民族傳統(tǒng)文學(xué)的融合與發(fā)展
在整體世界史觀的指導(dǎo)下,明確了民族文學(xué)處于向世界文學(xué)前進(jìn)的過程中,這就給了文藝家和批評(píng)家一個(gè)重要啟示:民族風(fēng)格不可能有某種具體的樣板,民族風(fēng)格應(yīng)該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活生生的東西,是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結(jié)合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中國(guó)作風(fēng)和中國(guó)氣派”,是豐富多樣的具體風(fēng)格中民族精神的印記。這種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質(zhì)、思維習(xí)慣,構(gòu)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礎(chǔ),表情達(dá)意的方式和價(jià)值觀,但也要在外來文化沖擊和自身規(guī)律的作用下,發(fā)生微妙的有時(shí)是深刻的變化。從前人們以女人纏小腳為美,以少年老成為難得,現(xiàn)在正好相反,便是觀念變化的證據(jù)。因而提倡民族化,決不是強(qiáng)迫文藝家遵循現(xiàn)有的某種規(guī)范,而是要他們從世界文明大潮中廣泛吸收有益的養(yǎng)料,充分發(fā)揮個(gè)人的創(chuàng)造性。只要文藝家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了生活中所蘊(yùn)藏的民族的精神素質(zhì),藝術(shù)上達(dá)到了內(nèi)容和形式的較為完美的結(jié)合,不論他采用什么風(fēng)格手段來組織題材,刻畫人物,其作品必定具有民族氣派。這正如魯迅評(píng)陶元慶的畫時(shí)所說的:“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彩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guó)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對(duì)于這種“內(nèi)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shí)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桔亡中國(guó)的民族性”的風(fēng)格,魯迅認(rèn)為“用密達(dá)尺來量,是不對(duì)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漢朝的慮儷尺或清朝的營(yíng)造尺”,而“必須用存在于現(xiàn)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yè)的中國(guó)人的心里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shù)”。需要指出的是,向“世界的文學(xué)”靠攏,并不是要抹殺文學(xué)的民族特性。世界的有機(jī)統(tǒng)一本有一個(gè)多樣性的前提。人類一方面越來越接近自由的共同本質(zhì),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自然條件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各民族在奔向自由的道路上總是采取了帶有自己歷史特點(diǎn)的方式。一個(gè)民族的詩人不僅必須對(duì)本國(guó)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他的出現(xiàn)還必須具有世界性的歷史意義。環(huán)顧西方作家,具有世界意義的人物并不罕見,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等等,無不以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天才,貼近人類的創(chuàng)作意識(shí),塑造了無數(shù)與全人類緊密相連的藝術(shù)形象。因?yàn)樗麄兗仁潜久褡寤馃嵘畹膮⑴c者,也是“人類一般生活的參與者”托爾斯泰語)。在這方面做得更自覺的是莎士比亞。他總是把戲劇沖突提高到“人類矛盾的高度”,“讓人類的要旨產(chǎn)生于它時(shí)代的歷史斗爭(zhēng)之中,并賦予它以一種如此集中、如此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的高度”。但是,我們不能對(duì)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作割斷歷史、脫離國(guó)情的類比。一般來講,中國(guó)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前閉關(guān)鎖國(guó)的封建經(jīng)濟(jì)生活,使得無數(shù)文人缺少西方世界乃至莎翁那種自覺。但是,談藝的第一原則是要看對(duì)象是否符合藝術(shù)規(guī)律。眾所周知,“形象大于思維”的現(xiàn)象,使我國(guó)許多古代作家贏得了生前不曾料想過的殊榮。這是藝術(shù)形象所包含的社會(huì)意義和思想價(jià)值超過了作家主觀認(rèn)識(shí)的有力的證明。
三、結(jié)語
總之,求同論證可以視為輻合思維,它能在提供的根據(jù)中得出有方向、有范圍的結(jié)論。求異論證又叫輻射思維,它能從一個(gè)目標(biāo)出發(fā),沿著不同的途徑去開拓,以探求多種答案。它不受固定方向、范圍的制約,能求答案于未知,更易有所發(fā)現(xiàn)。
作者:付曉 單位:遼陽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本文html鏈接: http://www.cssfps.cn/qkh/55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