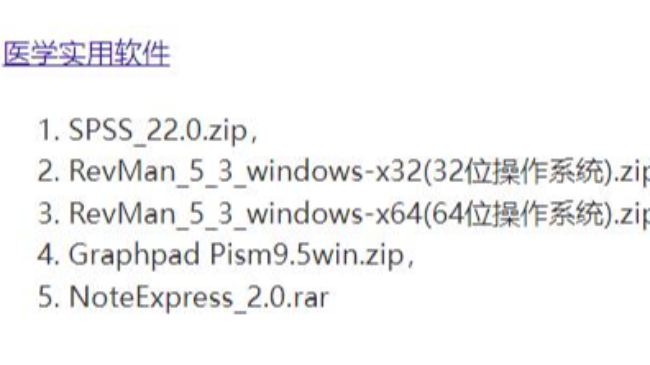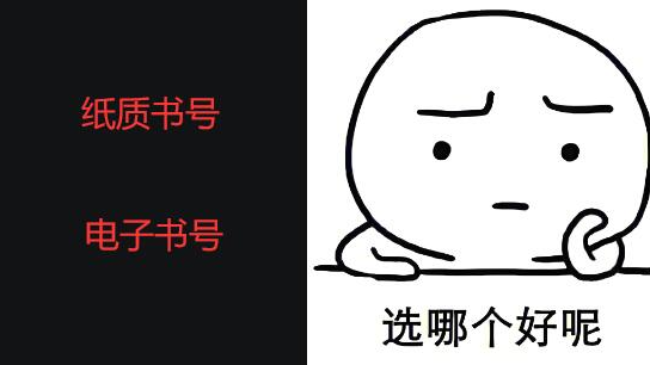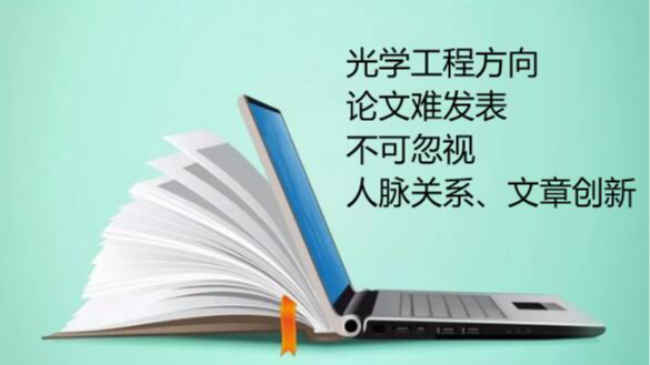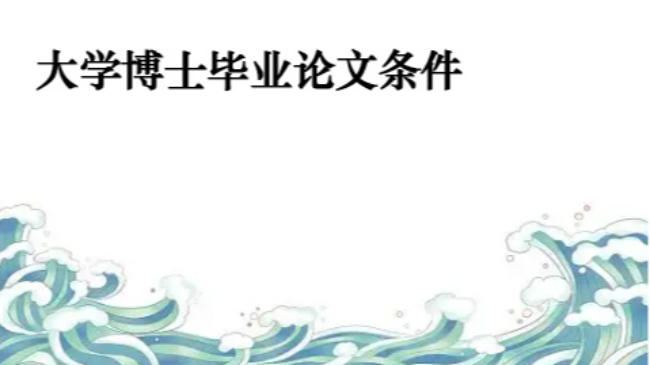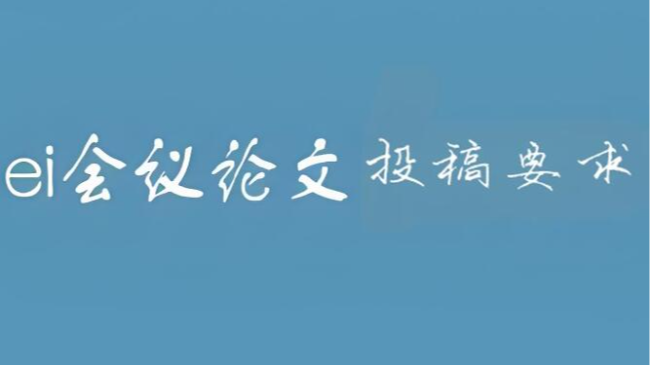農田發展權分配體制與保障體系建構
本文作者:周四丁 單位:湖南理工學院政治與法學學院
要建立實現基本農田保護供給面由非均衡性向均衡性轉變的補償移轉制度及舉措,構建激勵相容的利益分配機制,設計基本農田保護的經濟補償機制。[3]陳百明認為改進基本農田損失補償制度是保護基本農田的重要手段。[4]李邊疆基于公共物品私人供給的模型,構建了耕地保護過程中地方政府在個體理性支配下同整體理性進行博弈的分析框架,并據此對實踐中存在的耕地保護政策失效和政府間耕地保護意愿差異的現象進行了解析,認為地方政府在個體理性支配下的博弈行為是耕地保護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5]這些研究雖然探討了基本農田保護過程中農民的權益受損問題,并嘗試通過補償農民、監督政府等方式來解決問題,但如何補償才算合理,補償農民與監督政府如何才能落實,目前還缺乏有說服力的研究。筆者認為,只有以制度的形式賦予農民基本農田發展權,才能使農民的基本農田土地權益不受損失;只有建立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護農民的基本農田發展權益。因此,創設基本農田發展權,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有效監督的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才能真正保護農民的基本農田土地權益、保護基本農田。
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建設的必要性
制度建設是規范一切行為的基礎。土地發展權即改變土地用途或利用強度之權,這種權利的實質是土地權利人可以通過市場來配置土地資源,通過改變土地用途來獲得市場的平均收益。我國的基本農田的用途被限定為糧食生產,因而也就基本失去了改變用途的可能。從物權法的角度上分析,我國剝奪農民的基本農田發展權的過程是“國家通過嚴格限制農民基本農田事實處分權、基本農田所有權處分權、基本農田自主經營權等三項物權權能,對基本農田實行了最嚴格的用途管制,獨占基本農田發展權”的過程。[6]從實施程序的角度來分析,我國政府是通過“強化基本農田用途管理控制、強化征收審批程序”獨享基本農田發展權。[7]當然,國家獨享基本農田發展權的系列制度是為了保證糧食安全,我國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的成就,正是這些制度的價值所在。然而,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建設的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值得憂慮。
首先,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缺失限制了農民務農收入的增長。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僅50%左右,仍然有一半人口依然靠土地為生,務農收入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我國種糧農民的比較收益很低亦是不爭事實,“畝均凈收益僅在30元至80元之間”;而如果基本農田用于種植經濟作物,“經濟作物的畝均收入達到1433元”;[7]如果被征收,收入增加可達1000倍(盡管征收補償極低)。國家獨享基本農田發展權的制度,剝奪了農民根據市場需求自由支配土地資源的權力,使基本農田承包者無法達到種植經濟作物的收入水平,也無法達到被征地者的收入水平。基本農田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基本農田承包經營者本應有權在價格杠桿的引導下,種植比較收益高的農產品,從而合理配置土地資源,以期從市場上獲得社會平均收益。政府對基本農田用途的限制使基本農田的土地資源不能流動,導致土地資源在糧食生產方面的投入過大,從而導致糧食生產供過于求,由于糧食的需求彈性較小,供略大于求就會導致糧食價格較大幅度的下降或者長期低價,因而極易出現增產不增收的情形;同時,糧食生產增長刺激了對農藥、肥料、種子的需求,導致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不斷上漲。在糧食處于買方市場,糧食生產資料處于賣方市場的情形下,糧食生產者的收益被壓擠到很低的水平,從而限制了農民務農收入的增長。
其次,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缺失導致地方政府濫用征地權。基本農田發展權缺失使農民土地權利得不到制度性保障,為地方政府侵犯農民土地權益提供了方便,其中最嚴重的當屬地方政府濫用征地權。現有的基本農田制度安排將基本農田發展權完全劃歸國有,尤其是直接行使行政審批權、征地權的縣、市級地方政府所有。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中,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合法地征地將基本農田轉變為國有建設用地,并通過招、拍、掛的形式將其使用權轉讓,以獲得經濟利益。由于土地權利分配不合理,基本農田被征后的增殖收益分配不公平,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巨額的賣地收入,而失地農民所獲得的補貼相對于賣地收入顯得微不足道。“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既不比普通人卑鄙,也不比普通人高尚,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政府實際上是以“參與者”與“管理者”雙重身份進入征地博弈中,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政策必然會以保護和增進政府的經濟利益為目的。”[8]由于政府擁有基本農田發展權,并且可以通過征地、轉讓土地使用權獲得巨額經濟收益,因此,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考量自然容易濫用征地權,而不會考慮農民的意愿,其結果不僅是與民爭利,還會大量破壞基本農田,真正危及國家的糧食安全。這樣,地方政府因為征地處于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對立面。也就是說,國家獨享基本農田發展權是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和農民存在直接的、零和利益沖突,在強勢政府與弱勢農民的利益沖突中,地方政府會獲得經濟上的勝利,但是會失去民心而在政治上遭受失敗,最終的結果是政府與農民都失利。共贏的制度是利益平衡的制度,基本農田發展權需要在國家、集體與農民之間合理的分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關鍵在于構建合理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權益分配機制;農村建設用地流轉涉及國家、集體、農戶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其間任何一方的利益受損都會影響到建設用地的正常流轉。”[9]因此,只有加強基本農田發展權系列制度建設,賦予農民一定的基本農田發展權,才能使失地農民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城市化進程中受益;才能對地方政府的征地權進行監督,并抑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沖動。
基本農田發展權的分配制度建設
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建設的實質是賦予農民一定的基本農田發展權,其根本目的是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提高農民收入,發展農業生產。
首先,制定基本農田用途管理制度。目前,基本農田的用途被限定為糧食生產,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基本農田不被破壞,另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糧食供給。保護基本農田不被破壞依然非常重要,但是保護糧食安全的具體做法,需要進一步完善。換言之,需要在保護基本農田的前提下,優化基本農田的種植結構,滿足人們多樣化的農產品需求,提高農民的收入。在經濟落后的背景下,人們對糧食的依賴性很高。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農產品需求日益多元化,對特色農產品的需求上升,對主糧的需求反而下降。這也是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后飲食結構更加均衡的表現。因此,農業生產要著眼于人們需求的變化,合理利用土地資源,滿足人民群眾日益豐富的農產品需求。這客觀上要求在制度的規范下對基本農田的用途進行適當的調整,允許農民利用基本農田生產不破壞基本農田的經濟作物。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會引導人們在經濟作物生產與糧食生產之間進行土地資源的配置,這樣既能提高糧食的市場價格,又能豐富經濟作物的供給,既能提高農民的收入,又可豐富農產品市場。第一,定期適時調查了解糧食需求的變化,并將該措施制度化。糧食需求多樣化的滿足原本可以通過市場來解決,但是政府將基本農田置于市場之外,市場就無法自發滿足糧食需求的多樣性,基本農田的用途被限定后,基本農田對糧食需求的多樣性不敏感,需要政府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第二,實行基本農田耕種狀況調查制度。鑒于目前大量存在的基本農田拋荒現象、被占用現象、雙季改單季現象,政府應通過制度化的調查研究,及時了解糧食生產過程中基本農田的使用率。第三,完善土地流轉制度。通過土地流轉,可以引入外部資本,可以將拋荒地及低效率使用的基本農田集中起來提高使用效率。如湖南瀏陽淳口鎮的煙葉種植基地,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集中了大片基本農田,采用煙葉+晚稻的種植模式,既保護了基本農田,又豐富了農產品市場。第四,實現基本農田用途審定制度化。對于滿足糧食需求之外富余的基本農田,可以通過用途審定,在不破壞基本農田的前提下種植經濟作物;但是經濟作物的生產應處于政府制度化的監督之下,以確保基本農田使用符合規范。
其次,完善基本農田征用制度。我國現有的相關土地法律法規將變更土地性質的權利完全賦予給國家,“農民集體既無權主動將基本農田所有權轉讓給國家,又無權在國家有需要時拒絕轉讓其基本農田所有權”,[6]并且政府在征地過程中可以獲得巨額的經濟利益,所以,政府會濫用其征地權,以公共利益為幌子,隨意擴大征地范圍。雖然國家有耕地占補平衡的相關法律法規,但是這些法律法規只是確保耕地的總面積不變,而無法保證耕地的質量不受損失,更無法觸及耕地地理位置差異所蘊含的經濟價值的差異,而且占補平衡中,政府的謀利行為不受任何制約。因此,國家需要進一步細化征地的法律法規,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使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符合國家的總體戰略。第一,健全土地使用規劃公示制度。政府的土地利用規劃要向農民全程公示,使農民知曉規劃以防止地方政府以法規的名義欺騙農民,也可以使農民能主動抵制非法征地。第二,完善征地監督制度。對征地過程要全程監督,上級政府、媒體對當地政府的征地行為要全程監督,要使政府的行政行為全程處于陽光之下。只有制度化的監督,才能使監督更有效力,才能使地方政府消除僥幸心理。第三,完善檢查制度。要加強對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規劃執行情況的檢查,并明確違規處罰方案。只有讓地方政府承擔相應的違規代價,才能從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濫用征地權的問題。只有從健全法律法規入手規范地方政府的征地權,才能為保護農民的基本農田發展權提供制度基礎。
再次,制定土地出讓金分配制度。地方政府濫用征地權的根本動力是征地過程所獲得的利益,因此,合理分配土地出讓金,一方面可以降低地方政府政府濫用征地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社會公平。分配土地出讓金的總體原則是要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農田發展權。第一,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并使補償制度化。現在的征地補償標準只是補償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而并沒有補償農民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基本農田是農村集體所有,也就是由農村集體中的農民按份共有,征地需要對農民的基本農田集體所有權進行適當的補償,這是農民基本農田發展權的最直接的表現形式。補償的制度化是通過制度的形式規范補償的各個環節,使補償能落到實處。第二,要將部分土地出讓金上交給中央政府,以供中央政府建立專項基金用于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發展農業科技,從而提高糧食生產者收入,這也是農民基本農田發展權的表現形式之一。第三,應將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的使用納入地方公共財政,編入地方財政預算,接受地方各級人大的監督;同時,地方政府應提高土地出讓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比例,使農民真正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目前我國的財政支出正在由經濟建設型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這兩種財政支出的區別在于經濟建設型財政的主要支出是用于經濟建設,而公共財政的主要支出用于教育、社保、醫療等民生領域。但是目前各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不納入地方財政的預算與決算,由地方政府用于經濟建設。如果能將土地出讓金納入公共財政,可以為彌補地方政府公共財政的不足,為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財政支持,這也是農民基本農田發展權的間接體現。
基本農田發展權實施保障體系建設
創設基本農田發展權是農民持續增收的制度保障,但是這種制度需要有力量推動,地方政府就是這種無法回避、可以依賴的力量。這考驗著制度制定者的智慧,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既要限制地方政府的私利、保護農民利益,又要使地方政府有積極性地保護農民的利益,使地方政府由農民利益的損害者變成農民利益的保護者。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的制定意味著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使地方政府和農民由利益沖突雙方變成互利共贏的雙方。“利益沖突相當于觸發機制,正是在公權與私利出現沖突的背景下才會導致私欲膨脹、權力異化和機會漏洞。我國公共生活中的許多腐敗現象、不正之風、官僚主義等問題的背后實際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利益沖突,”[10]制度建設就是要消除利益沖突,尋求共同利益。韓非的“目標——交易”管理模式可以為如何建立地方政府與農民同利的基本農田發展權制度提供啟示,該模式對現代管理的啟發有三點:“領導者制定并堅守目標;通過交易的方式聚集實現目標所需的資源,建立交易規則;交易規則的破壞者主要是作為交易規則執行者的官員,需要以法術來監察官員以維護交易規則。”[11]該模式對基本農田發展權保障體系建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首先,中央政府應當建立農業生產發展目標體系。十六屆五中全會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要求,其中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宗旨。胡錦濤在2012年APEC峰會上提出:“我們應該加大農業投入,促進農業投資,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擴大糧食產能。要加強糧食交易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打造現代糧食物流體系,降低糧食儲存、運輸、消費環節全程損耗水平。要加大對農業生產、技術研發的投入,推廣應用新技術,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證食品安全和質量。我們應該穩定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防止過度投機和炒作,改善農業投資環境。”這是對農村生產發展的進一步解釋和定位,其核心是發展糧食生產、降低損耗和成本、提高農民收入。這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保護農民的基本農田發展權。圍繞這一總目標,需要制定落實該目標的目標體系。該目標體系應該由三個指標體系構成:第一,糧食生產指標體系。包括各地耕地、基本農田總面積,用于糧食生產的總積,用于可不破壞基本農田的經濟作物生產的總面積;拋荒面積,土地流轉規模與目標,糧食總產量等等。該指標體系可以計算出某個地方在一定時期內可用于集中生產經濟作物的基本農田的數量。第二,農業成本和農民收入指標體系。包括農藥、肥料、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糧食儲存、運輸、消費環節全程損耗控制,糧食價格增長指標等等。第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指標。包括農業科技的投入與產出,農業流通體系建設,農田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指標,基本農田提質改造等等。只有中央政府制定出相對具體的發展規劃,地方政府才能在規劃的指引下積聚力量發展農業生產,進而保護基本農田。
其次,中央政府應當建立地方政府農業生產發展考核制度體系。“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韓非子•人主》)是根據官員的貢獻而給予職務上的升遷和物質上的獎勵,基本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激發地方官員完成中央政府目標體系的積極性。“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韓非子•顯學》)分配制度與目標體系相配套,努力實現中央目標的地方官員得到相應的提拔和獎賞,那么,中央政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就會早日實現。“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韓非子•顯學》)公平可信、有利可圖的分配制度為人們提供實現個人富貴的理想途徑,是人們“不得為非”的根本保證。因此,中央政府應將地方政府農業發展目標完成情況納入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標體系當中,并將該目標體系的權重提高到能影響官員個人升遷與獎賞的程度。這就要求改變單純注重經濟總量增長背景下的GDP績效觀為在科學發展觀背景下的綜合績效考核體系。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很長的時間內都強調經濟增長,將GDP增長速度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的核心指標,這種政績觀在一定時期內有其價值,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GDP增長依然是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將GDP增長速度作為對地方政府官員考核的重要指標依然很科學,但是,不能再將GDP增長速度作為最核心的指標,而應當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建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配套的績效考核體系,應科學合理分配各個考核指標的權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基礎性地位,雖然為GDP增長做出的貢獻比不上工業、服務業,但是農業的基礎性地位不能低估、農業發展對保障農民民生的重要意義不能低估,保障糧食安全、鞏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發展農業生產所需付出的努力也不能低估,地方官員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不能低估,因此其在政績考核體系中的地位也不能低估。只有政府官員為發展農業生產、保護基本農田發展權所付出的努力能得到相應的認可與回報,才能改變農民與地方政府利益沖突的現狀,使地方政府與農民的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能使地方政府成為農民利益的有力守護者。
再次,中央政府應當建立地方政府農業發展監督制度體系。盡管建立了與農民同利的績效考核體系,但是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不會更改,只要有可能,地方政府依然有可能為了擴大自身利益而利用自身的行政權力欺上瞞下,最終侵害農民利益,比如,在耕地占補平衡中以次充好,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中虛報成績,在農業科技成果推廣中加重農民負擔等等。這需要政府加強監督,建立與中央政府農業發展目標體系、地方政府農業發展績效考核體系完全配套的地方政府農業發展監督體系。第一,加強民眾對地方官員的監督。農民是地方政府的服務對象,也是地方政府謀私利的侵害對象,因此,要賦予農民監督政府的權利。中央政府應將中央政府農業發展目標體系與地方政府農業發展績效考核體系廣布農村,使農民知曉政府的合法行為與不合法的行為,然后鼓勵農民依法監督政府,“而告私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韓非子•奸劫弒臣》)當全體民眾都監督地方政府官員,就會增加地方政府官員的違法風險。第二,通過審核檢驗地方政府的政績。“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韓非子•六反》)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官員虛報政績,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對官員的業績陳述進行核查,不能讓地方政府成為本地方發展數據的唯一生產者和最后生產者,當下我國“數字出官”的不良現象正是對地方政府陳述的績效信息缺乏必要審核的后果。第三,加大處罰力度。“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韓非子•六反》加大處罰力度就是增加官員的違法成本,官員在違法與守法之間權衡時,會進行違法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只有加大官員的違法成本,才能使官員主動放棄違法行為而自覺守法、服務于農業生產,進而保護農民的基本農田發展權。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基本農田發展權分配制度與保障體系建設作為保護農民的基本農田土地權益、保護基本農田的基礎性工作和治本性措施,必須努力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著力:抓制度完善,著力提高制度的科學性。這是制度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制度建設的首要條件;抓制度落實,著力維護制度的權威性;抓制度創新,著力增強制度的適用性。
本文html鏈接: http://www.cssfps.cn/qkh/270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