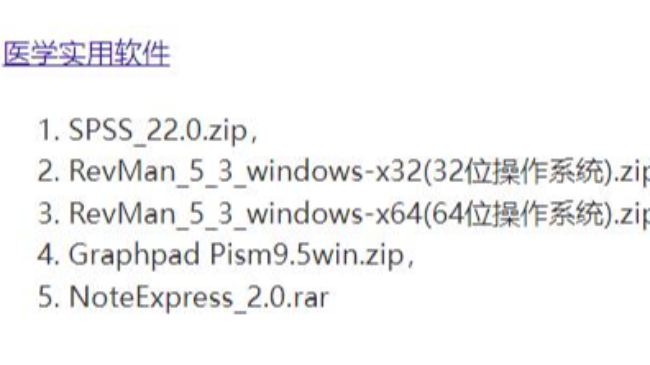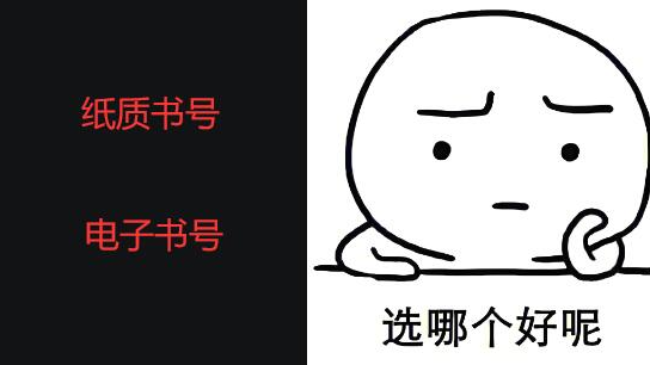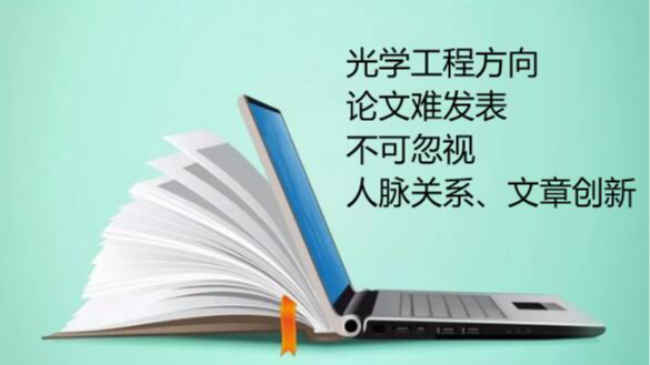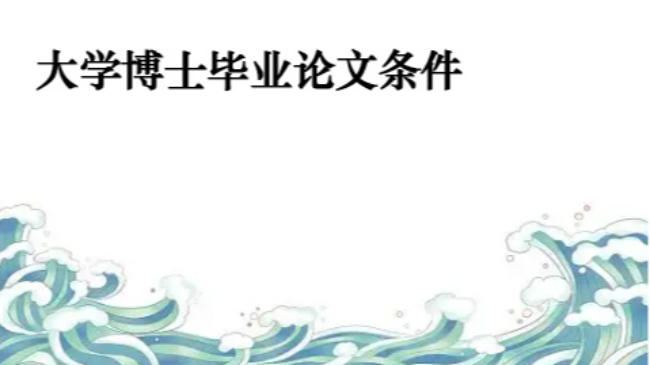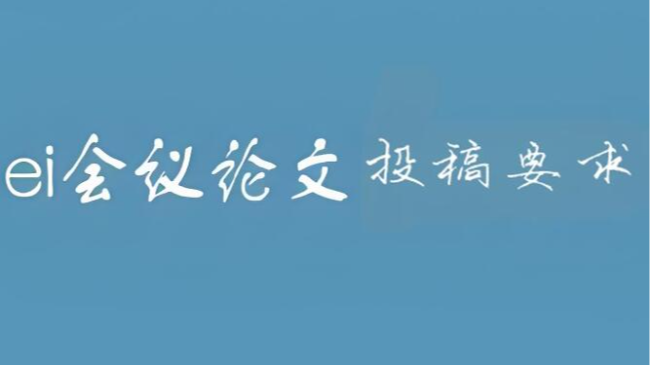農業社會與古代教育的關系
本文作者:吳龍、余珊 單位:南昌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南昌教育學院
人類在30多萬年以前,就開始了進化的歷程。在農業產生以前,人類依靠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果實、根莖等生存,過著餓則捕食、采食,飽則棄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動、植物的季節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類的生活是沒有保證的。人類的生存欲望和創造欲望使人類在距今約1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了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業文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農業生產的國家之一。前蘇聯學者瓦維洛夫通過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亞、印度、中國北部與中部山區、東非山區、墨西哥、秘魯等是幾個基本的、獨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農業。”[1]1954年,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經測定為7000年以前的遺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豬骨,88個灰坑貯存著糧食,有的窖底腐朽糧食厚達2米,經測定,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遺物。近年來,我國又在湖南澧縣彭頭山、道縣玉蟾巖、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巖等地發現了距今上萬年的栽培稻遺址。這些都充分證明,中國是最早出現農業文明的國家之一。中國源遠流長的農業文明不僅為中華民族的進化繁衍、發展強大提供了物質生活條件,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產生著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著中國農業文明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在當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國農業社會孕育了中國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國古代教育活動是從農業教育開始的。距今約1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類通過耕作、畜牧進入原始農業狀態。農業一旦開始,人類就需要將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進行傳播推廣。這就開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動。原始人群“為了供勞動更有成效,必須制造勞動工具。他們的勞動工具雖然簡單粗糙,經驗雖極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經驗和方法傳授給年青的成員,使他們知道群體生活和生產活動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動的記載,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寫到“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記敘,這些記載都反映了原始人類傳播農耕技術的教育活動。
原始教育活動是不可能與生產勞動互相分離而獨自存在的,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人類開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動,因此有了教育場所。古籍中記載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動的原始場所有兩種。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證為平坦、寬闊的場地,用來堆積捕獲物與農耕作物和聚會的地方,被認為是五帝時代的教育場所。二是“庠”,被認為是虞舜時代的學校,“庠”也是儲存谷物之處。《禮記•明堂位》中這樣闡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可見,不管是我們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動還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動,都是和中國古代的農業文明緊密聯系、息息相關的。古代文獻的記載和許多考古發現都說明中國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國農業文明的產物。
二、中國農業社會產生了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農思想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直接關系著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國家的政治穩定。人們依靠農業維持生存,統治者依靠農業維護穩定,農業在古代最具決定性的意義。因此,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把農業作為國家之本,中國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農恪印。在許多史籍中,都有重農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確提出“農本”觀念,李悝在魏國采取的政策是“盡地力之教”“禁技巧”,即發展農耕,約束手工業。墨子在他的論述中強調農業生產,“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聊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則“一谷不收謂之饉,二谷不收為之旱,三谷不收謂之兇,四谷不收謂之饋,五谷不收謂之饑。”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認為“工商眾則國貧。”漢代思想家賈誼在《論積貯疏》中論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這些重農言論的傳播是古代思想家們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他們的言論對歷代統治者和民眾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來說,唐代實行“均田制”,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允許農民擁有小塊耕地,同時在役期上規定農民的最高役期,讓農民有更多的耕作時間。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萬,比唐初增加數倍,開墾的土地面積大為增加、糧食充盈,這些都是唐朝統治者推行重農政策和農民接受重農思想說教的成果,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教育活動的成果。
中國農業文明也使得中國古代教育把是否知農、會農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標準。在《論語•微子》中有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的記錄,說的是孔子帶眾弟子周游列國宣傳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農,問其看到老師沒有。老農說,既不勞動,又不知道勞動知識,哪里配得上稱為老師。可見“四體”勤,“五谷”分是作為一個重要的人才標準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兩江總督曾國藩8歲時能讀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早年的讀書經歷及親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視對子女、親眷的勞動教育。他教育兩個兒子每天都要勞作,“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并且以同樣的要求對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給他們規定了什么時候起床,什么時候織布,什么時候種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織做的。曾國藩教育自己的子侄們:“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中國歷代史籍的許多記載都反映了中國農業文明對中國古代教育的內容和人才評判標準的影響。
三、中國農業社會蘊育了中國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點
農業生產是人們通過勞動來控制動、植物的繁殖與生產,以此來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需要。古代農業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呂氏春秋》“審時篇”指出:“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把天時地利的自然變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3]古代人們敬畏自然、順從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國農業文明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特點導致了天人合一成為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內涵,使中國古代教育追求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成為重要的教育目標。我們說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實體存在,天是說指自然及其客觀運動,人著重強調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觀世界。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論述,《尚書》有“惟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以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闡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亦云,“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莊子•田子方》)。“大地與我并生,而大地與我合一”《莊子•齊物論》典籍中又常有人與物相融的意境描寫。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擺焉……歲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大自然的變化影響人的情感變化,人與自然相生相感,這是與西方文明對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深深影響著中國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們如孔子、老子、孟子、莊子、董仲舒、韓愈、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等,他們都在教育活動中,著書立說,演講說辯,傳播著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認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賦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義。孟子認為“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調了人性與萬物的融合思想,也強調了認識自我與認識自然的統一。總之,中國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內容是豐富精深的,同時也對中國當代教育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四、中國農業社會產生了中國古代教育對家庭教育的重視
古代農業生產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民族生產生活的范圍極小。正如錢穆指出的,農耕民族“生長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墳墓安葬于此”,所以他們“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綿延”。[4]由于農業生產的空間局限性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限制,以及農耕發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傳的心理特征,使中國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為社會實施各種教育活動的最初起點和最基層的單位,使中國古代教育對家庭給予了更多的關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為古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們認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國平天下”,首先要“齊家”。“在封建社會,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長,他們負責家庭教育的主要責任,是家庭的準則。宋王弘官至尚書并進位太保,他知道自己應是人們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禮法,以致寫書信均有一定格式,這是他的家庭準則。后人都仿效他,稱為王太保家法。齊中書令王延之家教很嚴,見子弟要先規定時間。他的兒子倫之也用這個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長作為榜樣注意嚴肅是有一定道理的。陳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誨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規訓,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許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寫下了大量的“家訓”、“家教”類著作,以教育子孫,警戒后代。現存最早的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流傳最廣,被稱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廬的《治家格言》,又稱《朱子家訓》,勸人治家勤儉、安分守己,是影響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觀對中國的家庭教育產生重大的影響。曾國藩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響,他自己的家書又對中國近代、現代乃至當代都產生著更大的影響。錢穆對曾國藩推崇備至,認為是影響了他一生的重要經典,他稱曾國藩為“一大教育家”。李鴻章常以曾國藩“敬恕”二字誡其弟子。馮天祥也以曾國藩的“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抄錄過曾國藩的家書和日記,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學生。毛澤東還在延安時期建議黨員干部們都要讀讀曾國藩家書。
中國歷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歷史文獻的家庭教育觀念雖然有不少帶有封建社會的糟粕內容,但它們重視對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視營建良好的家庭環境,重視家庭結構的穩固,其中有許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對慈、善、孝、貞、悌等家庭倫理要求,對現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觀察我們今天的家庭教育,在教育內容上存在著重智育輕德育,在價值目標上存在著急功近利,在教育方法上存在著簡單粗暴等方面的一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繼承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優秀文化遺產,把具有普遍意義的家庭教育觀賦予新的時代精神并發揚光大,以促進個人成長、家庭和睦、社會發展。
中國農業社會與中國古代教育的關系是多方面的,以上僅僅是筆者的一些粗淺認識,我們將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農業社會與中國古代教育產生和發展的關系,以啟示我們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研究。
本文html鏈接: http://www.cssfps.cn/qkh/25873.html